谢冰莹与魏中天的深厚友谊
2002年第8期《人物》杂志 (文/钦 鸿)
香港中国文化馆创始人、总编辑魏中天先生把谢冰莹写给他的一束信函交给我,嘱我为之整理作注并编辑成书。我自然乐意从命。因为谢冰莹与魏中天不但相交长达七十余年,而且历经曲折坎坷、聚散离合,始终保持着真诚而深厚的友情,诚属极为难得;而他们相交之七十余年,又正值神州大地风云激荡、起伏多变的年代,所以他们的友谊,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丰富色彩。
谢冰莹早在20年代中叶便以一部自传体的《从军日记》风靡文坛。与她相比,魏中天的名声要略小一些,但他同样也是一位有成就的老作家和老出版家。他最初于20年代末期在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连载长篇散文《童年生活的回忆》。30年代初,又在上海发起成立新文学团体文友社,主编出版《文友》半月刊。嗣后,他一直写作不辍,出版了《污泥集》、《回顾集》、《论生活的态度》、《盛世才如何统治新疆》、《皇亲国戚及其他》等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从40年代起,便倾力于歌颂母亲的伟大事业,数十年来孜孜矻矻,坚持不懈,约请了海内外各界华人名流几百人撰写忆念母爱的文章,由香港中国文化馆出版《我的母亲》丛刊多辑,为弘扬炎黄子孙的热爱母亲、热爱祖国的传统美德,促进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华人的文化交流、感情交流,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杰出贡献。
谢冰莹与魏中天的结缘,最早在20年代中叶。1926年,魏中天在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为第六期学员。同年冬,谢冰莹在武汉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两人遂有缘缔结了远隔两地、彼此尚不相知的同学之谊。
北伐战争后,谢冰莹和魏中天不约而同地来到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读书,又一次成为同学。该校是一所革命的学府,在学校担任教员的有邓初民、黄药眠、冯乃超、李初梨、沈端先(夏衍)、郑伯奇等,同学中则有王莹、陈波儿、林烈(林默涵)、朱曼生(朱光)、杨纤如等人。据魏中天回忆,“每当社会上有什么纪念日,如五一、五四、五卅等,学生都参加示威游行”,“我们经常在大街的围墙上写革命的标语”(《忆木刻家温涛》)。在这座革命的熔炉里,他俩都经受了锻炼,建立了同志式的友谊。
谢、魏两人的再度晤面,是在1933年“闽变”期间。那年11月,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十九路军为主体,在福建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中央苏区联合反蒋抗日。谢冰莹和魏中天都参加了这一革命政府,谢还担任了宣传科长。魏早在1929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谢冰莹则是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之一,共同的进步思想基础和反蒋抗日斗争,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友情。

谢冰莹与魏中天在谢冰莹寓所圣母大厦门口
“闽变”失败之后,两人先后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再次同窗学习。机缘巧合的是,他们在东京还两次住在同一幢宿舍,先是在中东野桃园馆学生宿舍,而后住在阿佐谷樱花公寓,而且每一次都是比邻而居,可谓有缘之至!当时他俩曾在樱花树下留下过友谊的合影,可惜都在“十年浩劫”中被毁灭了。
从日本回国后,他们两人各自投身于抗战救亡的滚滚洪流,再见之时,已是1944年的冬季。当时谢冰莹偕丈夫贾伊箴在成都任教,而魏中天则劫后余生,刚从新疆狱中获释,在返回重庆时路过成都,无意中见到谢冰莹。这一次的重逢,给魏中天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致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她留我在她家吃年夜饭,吃的是老贾家乡山东水饺,席间,我们海阔天空各抒壮志”(《记谢冰莹》)。这是他俩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次晤面。嗣后不久,谢冰莹夫妇应邀赴台湾任教,从此终老海外,再也没有回到祖国大陆。
成都一别各天涯。这两个老朋友的再次握手重逢,竟是暌隔近四十年后的事了!离开大陆后,谢冰莹先是在台湾师范学院当教授,后应邀去马来西亚太平华联高中执教近三年,70年代从台湾师大退休后不久,便偕丈夫贾伊箴旅居美国旧金山。偌多年来,她生活平稳,写作勤奋,出版了各类体裁的作品集数十种,成绩斐然,名扬天下,而依然埋首笔耕,兀兀不已。她人在天涯,心系祖国,常常思念家乡和故旧亲友,却囿于种种原因不得乘风归来。殊不料在1980年11月间,她与阔别已久的老友魏中天竟在旧金山不期而遇。
魏中天这些年来经历十分曲折坎坷。他40年代后期在香港任海外通讯社社长,建国初期应谭天度之邀回广州工作,却不幸在那一场被称为“阳谋”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从此受尽屈辱折磨,沉沦达二十年之久。平反后,他急于见到遥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女儿,便申请赴美探亲。想不到在旧金山获悉老朋友谢冰莹的音讯,就写信相约会面。诚如魏中天所说:“我和她多年不见,如今一旦在万里迢迢的异国相逢,其快乐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了!”(《想到冰莹》)
从此以后,他们几次晤面,畅叙衷肠,热线电话也频频不断,有时还诉诸笔墨,通信联系。从1980年11月至1993年6月,魏中天收到谢冰莹的信件计56件。以他俩几十年的交谊,通信何止此区区之数,却由于时局动荡、命运浮沉,留存到今的竟只有这56封,怪不得魏中天视之若拱璧,不但精心珍藏,爱护备至,而且一直考虑想把它们付梓出版,以纪念他们之间历久而弥新的真诚的深厚的友谊。
翻阅这些弥足珍贵的信函,扑面而来的首先是谢冰莹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故国情思。她离开祖国大陆几十载,从来没有忘记生她养她的祖国和亲人。在一篇散文《故乡的云》中,她这样写道:“我一直站在船边看云,我的思潮起伏,也像海里的浪涛一般翻滚,冲击,发出伤感的叹息:我爱的是故乡的白云,湘江的流水,洞庭湖的波光,岳麓山上的彩霞,和青枫峡里的红叶、溪流……故乡啊,故乡,祝福你,别来无恙。不久我就要回到你的身旁。”所以,当来自祖国大陆的老友魏中天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久久郁结于心的怀乡之情便不可遏止地喷涌而出。她急切地向魏中天打听老朋友赵清阁、陆晶清、白薇等人的近况和通讯处,迫不及待地希望跟她们取得联系。在与魏的通信中,也一再向魏询问其他故旧好友的情况,想知道他们“现在何处?”“有几个儿女?”“生活还好吗?”如此等等,无限的牵挂之情溢于言表。魏中天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尽其所知,一一向她详作介绍,还千方百计地为她打听故友的下落。在魏中天的帮助下,谢冰莹先与赵清阁和陆晶清通上了信,便写信告诉魏说:“现在我已和赵、陆通信了,真高兴,不久白薇的地址找到后(赵会告诉我),我也要给她去信,那时更多一个老朋友了。”(1981年5月20日)为了满足她的愿望,魏中天在返回广州的第二天,立即写信向北京的孔罗荪打听白薇的地址,很快使谢、白两人恢复了联系。他还经常为谢传递信件,谢写给大陆诸多亲朋好友如赵家欣、杨纤如、罗青、吕器、梁兆斌等人的信函,大多是交由魏中天代寄的,以致谢感激地说他做了自己与大陆故友们之间的“桥梁”。
谢、魏两人通信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谢冰莹著作在大陆出版的问题。谢冰莹其人其作在三四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建国后由于复杂的原因而寂寂无闻。时至80年代,许多老朋友都不详她的生死情况,年轻一代则大多对她茫无所知。魏中天在旧金山与谢冰莹重逢之后,就有心做一番“启蒙”宣传。他一面撰写了散文《记谢冰莹》在香港、大陆的报刊上发表,一面则考虑促成在大陆重版谢的著作。从1983年11月至1985年3月的书信中,可以看到魏中天为四川文艺出版社重版谢的《女兵自传》一书所作的努力。由于大陆早些时候出版的《港台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集》一书,在选入谢的两篇散文时作了一些改动,使得她大为恼火,从此对大陆出版她的书非常抵触,后来态度虽然有所缓和,仍再三声明“如一字不改原著,可以出版,否则,我绝对反对!”魏中天居间调停,颇费了一番努力,才使得《女兵自传》顺利问世。魏中天的热心联络,可以说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为遥在海外的谢冰莹与国内读者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在通信中,谢冰莹对魏中天主编的《我的母亲》丛刊甚为支持。魏中天早在1948年香港出版《我的母亲》一书时,就将谢的散文《伟大的母亲》收入书内。四十年后,他主持出版《我的母亲》丛刊新一辑时,又收入了此文,同时还希望谢能再写一篇新的文章。谢对老友编辑出版丛刊续集,表示了莫大的关切和由衷的赞赏,她在1988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本来这次我还想再写一篇《我的母亲》,因眼痛,无法完成。这种资料,希望你再发出一批征稿信,每人都会写的,将来可以出三集四集乃至无数集,功德无量。”后来,魏中天果然对此事业一往无前,在新一辑之后,又相继编辑出版了新二辑、新三辑乃至新七辑。如今,他已届九三高龄,仍锲而不舍地在筹划着新八辑的编辑出版事宜。他之所以保持着如此旺盛的干劲,应该说与老友谢冰莹的鼓励也是分不开的。谢冰莹不但支持魏中天主编《我的母亲》丛刊,而且还向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编辑出版《我的父亲》。她在1989年1月28日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父亲的材料不会比母亲少。像这种书,是很可以感动万万千千的读者的,更可以使多少青年人知道怎么做父亲,怎么影响他们的未来的儿女。”1989年11月4日又说:“将来希望你再编一本《我的父亲》,我一定写一篇长文。”但是可惜得很,这一提议后来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
几十年的交往,加上恢复联系后的频繁联系,使得谢、魏两人的友谊更加深了一层。但尽管如此,两人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歧见和矛盾的。谢冰莹在1981年12月7日信中,对魏写的《记谢冰莹》一文写到他俩的通信次数提出异议。这看来是记忆上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他们在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从谢冰莹的信函来看,他们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看法两个方面。
如上所述,谢冰莹在30年代曾是北平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在福建参加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但几十年之后,她对这段历史却讳莫如深,在信中一再予以否认。1981年7月24日的信中,她说:“我不是左联发起人,因为教书,上课太忙,所以没有功夫参加工作。”又说:“我从来没参加人民政府活动,也没有被通缉过,更没受流亡之苦。”同年12月7日,她再次写信给魏中天强调说:“我从来没有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你参加,我完全不知),更没有反蒋,我是始终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孙总理和蒋总统的;否则我为什么要跑去台湾?”我们知道,谢冰莹一向是个热情爽朗、敢作敢当的人,此时何以竟判若两人?其实除了其斯时的政治倾向与彼时有所变化之外,还有一层隐情,便是不想让她那思想反动而顽固的老伴贾伊箴知道她的革命历史,以获得夫妇间晚年生活的平和与安稳。魏中天对她的态度自然是了解的,同时也能理解她的苦衷,所以虽然并不苟同她的观点,但仍做了自己也觉得可笑的事情,即按照谢的要求,在贾的面前大声对她说:“你思想这样反动,哪里有资格参加左联和闽变……”以使贾伊箴不起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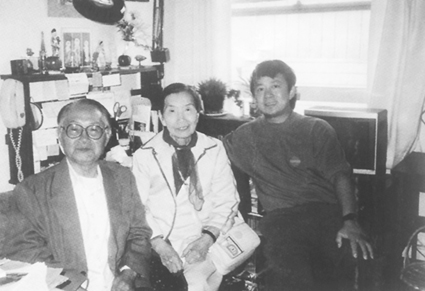
谢冰莹与魏中天1992年摄于谢家客厅
然而对于现实问题也即对于祖国大陆的现状的看法,魏中天却没有作出让步。魏中天与谢冰莹在异域重逢之后,便殷殷鼓励她回国旅游,探望亲人,会晤故友,也看看祖国大地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的面貌。后来,他又多次向她转达了众多朋友的同一愿望。但谢冰莹迟疑再三,始终未下决心成行,原因之一就是对祖国大陆还心存疑虑。有一次,她甚至还把这种疑虑、指责形诸笔端,公开发表。当魏中天从美国《世界日报》上读到她写的那篇题为《国破山河在》的文章后,立即针锋相对地在美国《源流》双月刊上撰写了《祖国没有破,山河更壮丽》一文,与她商榷。文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陆曾经发生过的极左浩劫及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对大陆的所作所为,撇开拨乱反正几年来的新生事象不谈,悉搬过时的事例”,是不可能作出公正评价的。文章最后,他殷切地向老友发出呼唤:“冰莹!我告诉你,祖国没有破,祖国的山河今天更壮丽!你是热爱祖国的,你总是希望祖国富强,我读过你许多充满爱国热情的篇章,前年我们在美国三藩市欢晤时,你也对我这样说过。所以很盼望你在你认为适当的时候,和贾先生同回祖国观光一次,深信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和你的许多读者,都会举起双手欢迎你们!而你也会像枯木逢春,在文艺领域里重新焕发青春,给祖国带来更大的贡献!”
虽然谢冰莹对中国大陆仍抱有一定的成见,但她在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上倒是毫不含糊的。她曾对魏中天就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她认为:“台湾一向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对不能分离。所谓‘台独’,在我看来,是死路一条!”又说:“祖国分裂已过了四十多年,我认为愈快统一愈好,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分久必合的,海峡两岸统一起来,国力就会更加强大,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都一笔勾销,赶快统一起来,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会赶上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魏中天非常赞赏老朋友在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的正确立场,随即撰写了《谢冰莹谈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及其他》一文,向祖国大陆的朋友和广大读者作了及时的报道。这篇文章无疑是谢冰莹和魏中天两人友谊史的灿烂的一页。这也说明,谢、魏的友谊,是建立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共同的深厚的挚爱之情基础上的,所以,他们可以被时空距离所遥隔,也可以就某些问题发生争论或互相宽容,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真挚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源远流长、悠悠不尽的。
2000年1月5日,谢冰莹在美国旧金山因病逝世。耄耋之龄的魏中天在悲痛之余,很想为老友做些事情。他本想在有生之年,把谢冰莹几十年从不中断的日记整理出版,却由于海天遥隔,他又年届耄耋,恐怕已难如愿以偿了。但是,谢冰莹写给他的这批珍贵信函的出版,也足以寄托他对谊交七十余年的老友的深沉的纪念了。
(责任编辑 李京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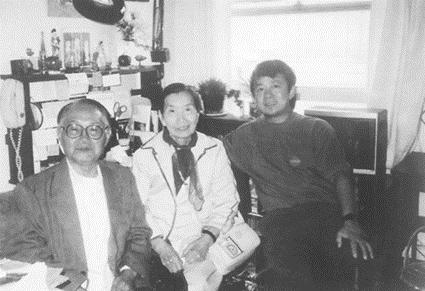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