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爷爷韦汉烈士
怀念我的爷爷韦汉烈士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们
□唯唯
我有一个爷爷。长眠地下整整71年了。
对我而言,爷爷是一份亲情,一份怀念。爷爷离我很遥远。但我时常想念爷爷。想爷爷,有时在睡梦中,有时在笔尖上,有时在回忆里。爷爷是我心头的痛,想到爷爷我就哽咽无语,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和我一样一生都在想念爷爷,只是到死都没有见到爷爷,因为爷爷死时父亲才一岁。
爷爷的名字叫“韦汉”。
爷爷是个历史名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22年初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党员之一。爷爷又是一个革命烈士,1939年春被国民党以“匪首”的罪名逮捕杀害,牺牲时47岁。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记得在1982年当地政府把“证书”送到家里的时候,用老辈人的话讲,就是那天老天特别“开眼”,我清楚的记得,那天天好像格外蓝,阳光特明媚。家里家外早就挤满了人,围得水泄不通的。家里像过年一样,锣鼓声,鞭炮声,欢笑声,声声入耳,好不热闹。我当时还是一个不知事的“懵懂少年”,但我分明感受到了乡邻们投来的羡慕的眼光。乡邻们讲,我长得很像爷爷的样子,日后一定会有大出息。听到这话,我心里就觉得像灌了蜜,甜滋滋的。这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爷爷就像一盏“明灯”,存活在心中,引领着我前行的脚步。30年来,一直不敢忘怀,也不能忘怀。
我对爷爷的记忆是陌生的。很久以来,愧于对爷爷了解不够,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爷爷的思念与日俱增,想了解爷爷的欲望愈加强烈。
爷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中国革命做过什么贡献,有过怎样的传奇人生,我等后辈又能为爷爷做点什么?诸如此类,许多疑虑萦绕在心尖脑海,挥不去,剪不断,理还乱。
近日偶阅家里的一部家书——《韦氏宗谱》,发现内有爷爷的“遗赞”:倩君名汉,学术可嘉,卒业师范,热忱日加,教授高校,六载无差,从来勇士,为国为家,旷观世界,宜保中华,兴亡负责,希望甚奢,成仁取义,牺牲无他……一个胸怀大志,敢于成仁取义的“豪杰勇士”形象赫然耸立在我的眼前,不禁对爷爷加深了几分敬意。
当然,爷爷是不幸的。爷爷的不幸又带给了家庭的不幸。文革那场史无前例的“人间劫难”,爷爷被冠以“土匪”“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父亲成了“反革命崽子”被红卫兵、造反派批呀,斗呀,最后被折磨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从此“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沦为了一个“时代牺牲品”。妈妈整日以泪洗面,姐姐被迫选择一桩不幸的婚姻……从此家里也像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再也没有了笑声。
只是痛苦和灾难有时也是一笔财富,经历过之后会让人变得更加坚强。风风雨雨,起起落落,这就是人生吧。
1979年,一个历史性的“春天”到来了。这一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爷爷的“不白之冤”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各地党史部门也努力为爷爷收集整理事迹资料,如原衡阳毛主席纪念地办公室的杨树发同志、衡阳“湘南学生联合会”陈列馆的刘淑敏、赵湘平、陈文质三位同志(他们当时都是副馆长),仅仅为了爷爷的两张照片,于1979年12月、1980年2月两度外访到县里和家里,原县文化馆的荆树藩同志为收集爷爷的资料,不辞辛劳,四处奔波,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这些事,仿佛还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他们的执着真情令全家十分感动。至今家里还存着他们写给父母的信,尽管时光飞逝,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信纸也已经发黄变烂,但珍藏的意念始终未变。1982年省政府又追认爷爷为“革命烈士”。我想,这对爷爷也是一种告慰吧。
爷爷的一生有许多故事。如在少年时代,有次两个学生在班上打架,把书桌都打坏了。爷爷就讲:你们在学校不好好读书,还打架打坏书桌,看你们怎么学习。说罢自己动手把书桌修好。爷爷的公德心自此显露无遗。还有一次,在县立高小,一个学生是富家子弟,常骑马来读书,为的是到学校“显摆”,爷爷看不惯他的“做派”样子,就批评他,对他讲:学校是圣洁之地,老师都是走路,没有坐车骑马,你是学生,你这样算是尊敬老师吗?迫于爷爷的“威慑力”,从此以后这个学生就不敢再骑马上学了。
据长辈回忆,爷爷从小就天资聪颖,熟读经书,放学回家后常在一间“水砖”房里读书写字。爷爷有个大墨盘,外方内圆的,乃祖传之物,爷爷视它为“珍宝”。墨盘总是盛着满满的墨水,墨水是爷爷亲手用墨棒磨好的。爷爷读书过后就会练练毛笔字。那个时候多是用“香包纸”,一写就是一撂。爷爷写字有个习惯,喜欢用两张纸折起来再写。爷爷的毛笔字写得好,“溜熟”得很,村里的红白喜事都请爷爷去写“对子”。爷爷肯帮忙,从不收钱,也不吃人家的饭。村里人讲:这个崽心肠好,帮人做事还要倒贴“人工”和“墨水”。爷爷写“对子”不“打”草稿的,随“肚”出,随手就来。在乡邻眼里,爷爷就是个“满腹诗书、满肚‘墨水’”的“文人”“秀才”。爷爷还喜欢写一些文章交给老师,老师最喜欢他了,跟他讲:你顶聪明的,希望多写文章,写好文章,他日定会有出息。爷爷点点头,将老师的话铭记在心。
参加革命以后,爷爷和毛主席有了交往。早在省立三师求学期间,作为省立三师的“精华”,爷爷就积极参加声援“五四”爱国运动,发起组织“湘南学生联合会”和“学友互助会”、加入进步团体“心社”和“马氏学说研究会”,成为最初加入“湘南学生联合会”和“湘南学生联合会”核心中的核心——“心社”的18位核心成员之一,经蒋介石最钟爱的“弟子”、北伐名将、“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衡阳第一个党小组--中共省立三师小组组长黄静源介绍,由毛主席亲自吸收入党,任“中共湘南第一支部”秘书,直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24年爷爷受毛主席的委派从安源回到家乡开展建党和农运工作,还经常和毛主席通信,直到长征开始,毛主席还复信给爷爷,信中写道:首经(爷爷的“字”号),我已离开江西瑞金,望多保重……润之。1928年爷爷在广西避难期间还给毛主席写诗,还用“手抄本”抄回家给乡亲,继续鼓动革命。其中一首是:太阳出来一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百难之中救中国,人人说他是英雄。由此可见爷爷和毛主席之间的深厚感情。
爷爷从安源回到家乡江华后,江华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杨霖,不仅嫖赌成性,而且破坏师生革命活动。爷爷决定开展“驱杨”斗争。经过充分的准备,爷爷指示学生会组织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在“劝学所”门前静坐请愿,要求当局罢免杨的校长职务。县“劝学所”被迫接受师生的要求,将杨调走。并于1926年春任命爷爷为代理校长,从此县立高小成为江华县党的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县立高小任教期间,爷爷白天则坚持上课,晚上就一顶斗笠,一身麻布青衣,走村串户开展革命工作,常常是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餐的。爷爷一心扑在革命上,根本无暇照顾家里,就是在邻村金田小学教书时也很少回家,对家里亏欠的实在太多太多。有时奶奶责怪他,他就耐心进行解释。他曾自嘲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待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好好补偿他们”。爷爷这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至今还深深镶在家乡人民的心里。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目睹蒋介石政府实行消极抗日政策,令在瑶族中享有很高威信、又富有爱国豪侠之气的冯绍异伤心不已。这一日,冯绍异心里实在闷得慌,便在寨子里兜圈,当他来到学堂前,却听见新来的“先生”在讲当今外面的新鲜事。这“先生”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江华县执委书记的爷爷,湘南暴动失败之后,隐蔽于广西,1935年才回到江华。冯绍异心里想:韦先生或许有些名堂,何不向他讨教一番?
于是,冯绍异决定请爷爷吃饭。
爷爷也不拘礼,傍晚如约来到冯家,二人推杯论盏,对饮起来。酒至半酣时节,冯绍异突然叹出一口大气,似有难言苦衷。爷爷也不作声,自顾端了酒一饮而尽,热辣辣的目光望了冯绍异好一阵,才用手指蘸酒在桌面上画将起来。冯绍异疑惑间,爷爷已停手了。冯绍异急忙趋前细看,两行龙飞凤舞的草书赫然在目:“挥弋斩倭寇,援共锄汉奸。”
冯绍异肃然起敬,心想:他连我的心里都看得穿,真英才啊,定能助我。便说:“韦先
生,你以为怎样才可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唤醒民众,实行全民抗战。”
“我想组织瑶族抗日军,你看如何才搞得成?”
“现在全面抗战热情高涨,国民党政府也不致于公然反对抗战。要组军应以取得合法地位为最好,不然他们就有借口加以阻止和镇压。”爷爷站起身踱步分析,“取得合法地位的有利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瑶族的特殊性,一个是你跟谢县长比较熟,上次他不是来看你了,要争取他的支持。”
冯绍异听着听着,多日来的愁眉舒展了:“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按你讲的这么办!”
此后三日爷爷闭门不出,帮助冯绍异起草了一份报告。爷爷将其定为《湘南瑶族请缨抗日报告》电呈省政府。说瑶族也是中华各民族之一,要担负起杀敌救国的责任。称湘南瑶族同胞志愿参军的可达10万之众,因瑶族的特殊性请求组建抗日军。报告很快便获批准。瑶族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吓慌了国民党顽固派,于是下令逮捕冯绍异。冯绍异被捕后,爷爷奋笔疾书,代表瑶汉群众上诉省政府,揭露事实真相,历数了“汉奸甘作倭奴之鹰犬,设计摧残热心救国志士”的罪行,要求惩办汉奸,开释救国志士冯绍异。1939年冯绍异出狱后,回到江华继续奔走大瑶山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准备重新组军。不料,
原中顾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从小受爷爷的影响最大。1924年爷爷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江华,在县立高小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建党和农运工作。江华是爷爷的学生,江华在自己的回忆录《追忆与思考》一书中描述,在学校,爷爷经常向学生传播外面的新思想、新思维,讲授革命的道理,介绍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阐述中国走革命道路的必要性。有一次,共产党员、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回家探亲,受爷爷之邀在县立高小向进步师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形势,进一步开阔了江华的视野。从爷爷那里,江华知道了“外面有个马克思,中国有个毛泽东”,从此坚定了他走上革命道路不回头。
……
不过,爷爷牺牲时的情景最令人感慨,如今回想起来仍叫人唏嘘不已。那天,爷爷刚从广西避难回来,穿着一件灰色长衫外加短褂,正端着一个铜盆从屋里出来倒水,刚到屋门口就被埋伏在外面的一个叫“刘毛狗”的国民党士兵认了出来,并大呼:抓住他,快抓住他,他就是“共匪”韦汉,别让他跑了,快……见状,十几个士兵随即凶神恶煞般地扑上去,将爷爷死死按住然后五花大绑后抓走。太爷爷闻讯赶忙从屋里跑出来,大声呵斥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抓我儿子,我儿子犯了什么“皇法”?但无济于事。当时太爷爷抱着襁褓中的父亲,父亲才一岁大,还在沉睡中。村里的一些有识之士听说爷爷被抓捕后,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马上喊人营救,不料追到途中就听见枪声响了,当时他们就预感到大事不妙,猜测敌人可能对爷爷“下手”了。果然不出所料,当他们赶到时,爷爷手捂胸口,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永远闭上了眼睛。他们把爷爷抬回村里后,尸体被停放在一个“堂伯”的田里,而后安葬在村前的一座茶山上面,直至今日。
据说爷爷死后,爷爷的一个学生来接任县长职务。到任后就问:我有一个老师叫韦汉,我想去看望他老人家。他老人家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情很深。此次赴任盼能见上一面,深表荣幸,不虚此行。知道爷爷已经遇害后,竟然抱头痛哭,连说:学生来晚了,可惜!可惜!实乃革命之不幸也。第二天他就带了“六十条抢”来村里,村里人还以为又是“梁子兵”来了,吓得都跑了。他就讲:你们不要跑,我是特意来看我的老师韦汉先生的。日后我会为他报仇的……
爷爷的一生建立了许多革命功绩。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即受党组织安排,和同为湘南学联骨干的蒋先云、何宝珍等到安源,协同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了安源工人罢工运动,取得胜利。是年11月,和蒋先云、贺恕、刘东轩、朱舜华等又被派到水口山铅锌矿,组织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历时23天的大罢工。他们一到这里,很快建立了党团组织,爷爷任团委书记和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任党支部书记兼工人俱乐部主任。年底,举行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它是继“二七”大罢工之后最成功的一次罢工斗争。1924年1月,回到江华开展建党工作,以县立高小为阵地,先后秘密发展沈成平、程芳、胡青松等9人入党。1925年5月创建永州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江华支部,任书记,隶属湘南特委。1927年1月创建永州境内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江华地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隶属湘南特委。帮助改组国民党江华县党部,担任常务执行委员。秋收起义后,组织湘南四县总暴动,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任主席。同时建立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组织领导了全县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爷爷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共永州地方组织的创始人,湘南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是江华革命的“播火者”和农民运动领袖,是湖南工运、农运、学生运动的活动家和组织者,与李启汉、陈为人、蒋先云、何宝珍、王涛等一道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永州籍最著名的8位烈士之一。爷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的功绩已被载入史册,成为人们心目中不朽的英魂。
30年来,我对爷爷的思念总在不经意间勾起。此时此刻,当又一个清明到来的时候,我除了对爷爷倍加思念以外,还夹杂着自责、忧伤。回想爷爷牺牲71年来,至今烈士墓还是一个“土堆堆”。特别是听到当地的一个小学校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在今年的清明组织师生去祭奠爷爷,却又找不到烈士墓在哪里时,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下的痛。我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愧,无地自容。这么多年来,除了清明去爷爷坟前修修墓,堆堆土,烧柱香,好像并未把爷爷真正记在心里,放在心上,自己并没有为爷爷做过什么。我恨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因为一直心存侥幸,总以为爷爷不属于他个人,他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属于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坚信政府最终会采纳自己的建议,帮许多像爷爷一样的革命先烈修建烈士墓或烈士陵园。毕竟这些革命先烈们,他们赴汤蹈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我们没有资格,更没有理由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才是托起中华民族不朽的“脊梁”。不管怎样,先驱们的“生命力量”不容被忽视。忘记他们就意味着忘本,忘记他们就意味着背叛。应该为后人留下一处为先烈们“下跪”的地方,让先烈们在九泉之下“过得幸福,有尊严”。给英烈以告慰,给良心和子孙一个交代!这是我等后辈应该做的事情。
也许我会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只是父亲,盼望了几十年,直到去年去世前还紧紧抓着我的手不放,千叮咛,万嘱咐,对我说:崽呀,你一定要帮你爷爷修墓,一定呀!我的鼻子就酸酸的,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
在我心里,父亲拖着几十年的病体,顽强活到现在,每次回家看到父亲熟悉的面容,听着父亲叨唠的话语,总以为父亲不会轻易离开我们。不曾想到这次父亲走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父亲望眼欲穿,从花开等到花谢,从黑发等到白发,最后还是带着深深地遗憾,怅然离开。
“为人子未能尽孝”。父亲的灵魂会安宁吗?
不知今年的这个清明,我是否还有勇气去祭奠爷爷。也许,为了这份不曾忘却的纪念,我还会继续等待,等待爷爷修墓的那一天的到来。就在昨晚,我梦见自己在烈士陵园里,爷爷的墓碑立于苍松翠柏中,小女则一边狂奔,一边呼喊,“太太,太太”。我们全家都流出了心酸而幸福的泪水。
这不会是梦!因为有些人,有些事注定是不会被遗忘的。他们终将被载入史册,彪炳春秋。
……
爷爷,您在天堂过得好吗?
爷爷,您安息吧。
2010年3月于瑶城江华·盛园家中
附:
“湘南学联”——“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是我党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湘南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心,是毛泽东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处所,为湘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和革命运动的开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学联的负责人,无一不是共产党员;驻会工作人员,不是党员,便是团员。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撒遍湘南各地及外地。湘南24县党的创始人和县委(或特支)领导人,差不多都是旅衡学生,不少人还担任当时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雷晋乾、陈芬、陈奇、高静山、韦汉、李一鼎、黄义藻、刘泰、邓宗海、夏明震、刘寅生、胡世俭、何汉、戴彦玺、袁痴、贺恕、黄亨明、向大复、乐开梁、贺辉庭、胡仕虞、向大名等。他们在湘南各地创建党组织,发展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斗争,使革命的烈火燃遍湘南大地。
湘南学联,从1919年6月创建,至1927年5月“沁日事变”结束,历经8年共16届。她,功勋显赫;她,群星璀璨。翻开湘南革命英名录,学运骨干占了300多。其中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李启汉、陈为人、何孟雄;有“心社”创始人,湘南学联两届总干事,安源、水口山两次大罢工领导人,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北伐名蒋先云;有著名学运、工运领袖典静源、唐朝英;有安源工运领袖、中共三届中央执委朱少连;有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委员长唐鉴;有在牺牲时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就义诗而饮誉中外的夏明翰;有在湘南暴动中建立卓越功勋的胡少海;有参加井冈山和湘、鄂、赣斗争的名将陈奇、曾中生、李天柱;有坚持正确路线而被错整为所谓“邓毛谢古反党集团”之一的谢给俊;有同李大钊一起上绞刑的方伯务;有同王荷波一起就义同埋一穴同共一碑的北方委刘惕庄、杨鹤云;有抗日名将谢翰文、王溱;有女中豪杰何宝珍、伍若兰、卜仁贞、朱近之;有夫妇(刘泰夫妇和李一鼎夫妇,蒋先云、李祗欣夫妇)、兄弟(曾令钧、曾令铨)、兄妹(戴彦玺、戴彦凤)、姐妹(李洁、李广)、叔侄(罗子平、罗俊逸)都是为革命献身的;有为革命奋斗终身并献出5个儿女的贺恕、朱舜华夫妻;更为悲壮的,如:夏明翰和弟弟夏明震、夏明霹、妹妹夏明衡、外甥邬一之,皆为革命就义;三师范校长、湘南学联指导者、被称为革命摇篮的女保姆蒋啸青与儿子蒋东群、弟弟蒋次青、堂弟蒋式令、妹夫谢维俊等,均为革命成仁。
湘南学联16届、111名总干事(有3人连任两届,1人连任三届)中,有7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被称为湘南学联核心的核心—省立三师的“心社”,共有成员30人(韦汉为最初加入的18位成员之一),这些人都是省立三师的精华,其中烈士有21人,占2/3强。
湘南学联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湘南地区的传播、党团组织的建立、工农运动的兴起以及整个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革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不仅有许多学联成员,为革命事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先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成了中华民族史册上百世流芳的著名烈士;而且有许多学联成员在建国后为我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如:陶铸、黄克诚、江华、曾希圣、张经武、张平华、伍云甫、张际春、唐天际、曾志、周里等等。这是湘南学联为中国革命贡献的一笔宝贵财富。她为革命立下的功勋永不磨灭!
“心社”——“心社”是“五四”运动和马列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影响下,于
一、“心社”的宗旨。
“心社”尊崇唯物主义史观,他们的首先标准是“舍己为人,立社为公”,倡导“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并广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二、“心社”的组织和发展
“心社”的组织设总务、经济、编辑兼书记三股。开始组织者为贺恕,总务主任为蒋先云、刘通著等。“心社”对社员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初成立时为18人,最多时成员为30人,即贺恕、蒋先云、黄静源、刘通著、蒋啸青、赵楠、韦汉、雷晋乾、唐鉴、唐朝英、袁痴、李恒青、罗严、黄逵、高静山、曹亨灿、彭章达、曾克家、黄益善、杜家俊、黄传琛、姜敬祥、唐孝明、黄谦信、雷腾宇、李俊、李祖莲、雷克长、江静邦、蓝世凯。
三、“心社”的主要活动
“心社”成立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和发展,积极组织领导“心社”成员和革命群众从事革命活动。
1、传播马列主义,推进新文化运动。“心社”在“新民学会”的影响下,采取多种形式传播马列主义。贺恕、蒋先云在教师蒋啸青、屈子健的资助下,发起设立三师文化“书报贩卖部”,除长沙新文化书报社分销外,还向北京、武昌、上海等地购进大批进步书刊。在学生中广泛传读的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心社”还编辑了《明星》、《先锋》、《三师周刊》,油印发给社员和校内外进步学生阅读。同时,积极筹办“衡阳文化书社”,组织“马氏学说研究会”、“星期日讲演会”,散发革命传单。这些社会活动使同学们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罗素、杜威、张东荪等人在湖南兜售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货色,起了抵制作用;为党、团组织在衡阳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还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2、组织“心社”成员参加驱张运动。“五四”运动中,皖系军阀张敬尧(湖南督军兼省长),为了取媚日本,以武力解散省学联,镇压维护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凌辱学生,殴打教师,激起湖南人民无比愤怒。毛泽东同志以“新民学会”的会员为骨干,以重新改组的省学联为基础,联合各界人士组织驱张请愿,分赴省内外,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当“驻衡阳驱张请愿团”来到衡阳后,把“心社”成员蒋先云、黄静源同夏明翰负责的联络教育界、女子救国会、国货维持会、劝学会、农会、商会发起参加请愿活动。同时,为查办张敬尧,向北京军政府及全国发出了十次通电,举行数十次集会和游行,驱张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3、兴办工人夜校。在湖南省第三师范学校办了第一个工人夜校。组织工人识字,提高文化素质和阶级觉悟,培养了大批工人骨干。
4、培养骨干,建立党组织。1921年10月中下旬,毛泽东来到三师,召集“心社”负责人蒋先云、刘通著等人听取该组织的情况汇报,指出:“长沙是新民学会,你们是‘心社’,都是进步组织。”并在“心社”骨干成员中发展了坚定信仰马列主义的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4人入党,建立衡阳第一个党小组--中共三师小组,由黄静源任组长。此次,毛泽东还从“心社”成员中发展了一批先进青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充实党的力量,衡阳党小组从1922年初以后,继续发展了“心社”成员韦汉、罗严、刘通著、袁痴、唐鉴、雷晋乾、高静山等人入党。1922年5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心社”成员悉数加入了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衡州地方团也在三师附近的东山庙成立,团员40人,“心社”成员达一半以上,韦汉被选为衡阳水口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委员会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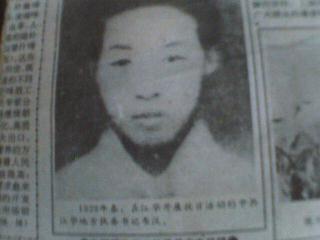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