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意立宪”
1903年是任公前后思想的分界线。是年,30岁的梁任公有过一次美洲行,长达十来个月。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梁氏立场彻底转变,从依违于立宪与革命,到放弃革命,一意以立宪为己任。接下来,前此发生在任公身上的“黄李之争”,便实实在在演变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辩论。任公则几乎是以一个人的力量与对方一个团队较量。
考量任公转变,原因固多,就他对现实观感而言,此点当予注意。民元之际,任公归国,面对报界,他这样解释自己当年所以弃革:“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
这里,梁启超尤不满于学生介入革命。他在一篇《答飞生》的文中表示:“自东京学生运动之义倡,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
还在世纪初,任公即反对后来一个世纪愈演愈烈的学生运动,堪为卓识。然而,他没料到的是,日后几年,他自己就输在这些他所反对的以运动而废学的留学青年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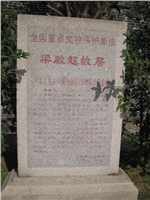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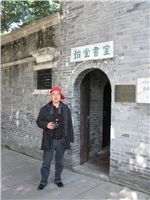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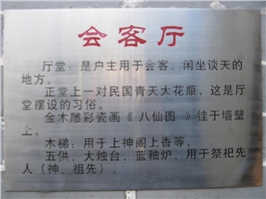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