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若彬外交生涯
加入外交部
麦若彬在1958年投考公务员,同获内政部和外交部取录,但他选择加入后者。[3]投身外交部后,他最先获安排在伦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一年,随后再由外交部安排乘搭头等邮轮前往香港,在1959年至1960年间于香港大学进修中文。[3]学成后,麦若彬自1960年至1961年在中国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任职三等秘书,当时的驻华代办是施棣华爵士,而参赞则是尤德。[3]麦若彬在1962年返回伦敦外交部本部,负责韩国事务,在1963年,他一度出任时任掌玺大臣希思的助理私人秘书,但同年10月希思改任贸易委员会主席后,他返回外交部负责亚拉伯-以色列事务。[3]
本身有意大利血统和懂得意大利语的麦若彬在1964年获外派往罗马的英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出任二等秘书,随后升任一等秘书。[2]在1968年,他第二度前往香港,担任时任港督戴麟趾爵士的助理政治顾问,同年外交部改组为外交及联邦事务部。[3]麦若彬在1970年至1973年返回总部,以一等秘书身份任职于人事行动科,负责内部人士与升迁事宜,后来于1974年至1975年间出任西方组织司副司长,专门处理北约事务,任内亦参与筹组欧洲安全暨合作委员会(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3]在1975年至1978年间,他在哥本哈根的英国驻丹麦大使馆出任政治参赞兼大使馆主管。[2]
香港前途谈判
参见:香港主权移交
在1978年,麦若彬返回外交部本部,担任香港及常务司司长,主管香港事务。[3]当时香港政府和英国的工党政府正因新界租约将于1997年届满,担心港府批出的地契不能过渡1997年,因而促使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在1979年接受邓小平邀请访问北京,继而标志着香港前途谈判的开始。[4]同时间,工党政府在1979年5月倒台后,麦若彬亦在同年年尾改任远东司司长。
[3]

![]()
英揆戴卓尔夫人最初坚持英国拥有香港主权。

![]()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则坚持中国要在1997年取得香港主权。
保守党上台执政后,新任英揆戴卓尔夫人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强硬态度,而她的内阁阁员亦多次前往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方交涉。其中,麦若彬曾在1980年3月随国防大臣皮姆(Francis Pym)访问中国,这是英国历来首度派国防大臣出访中国。[3]翌年4月,他又随外相卡灵顿勋爵访问中国,期间卡灵顿曾就新界租约事宜与邓小平交换意见。[3][5]在1981年,麦若彬复获任命接替卫奕信出任港督政治顾问,不久以后,尤德爵士在1982年5月接替麦理浩出任港督,两人遂与身在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联手处理香港前途问题。[3]
在这时候,戴卓尔夫人刚在福克兰战争战胜阿根廷,令她有更多时间关注香港事务,并且在同年9月于北京会见邓小平,中英两国随后在同年10月正式就香港前途展开非正式的首轮谈判。[6]不过,在谈判中,一方面中方坚持收回香港,而另一方面,英方则坚持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仍然有效,并强调英国拥有香港主权是理所当然。两方各不相让,使到首轮谈判陷入胶着状态。[6]一直到谈判后期,英方代表柯利达成功游说戴卓尔夫人,就主权事宜在谈判桌上让步和妥协,才促成第二轮谈判的召开。[6]
戴卓尔夫人在1983年大选连任后不久,中英两国同意召开第二轮谈判,双方在7月初公布代表团的成员名单,其中英方团长继续由柯利达出任,而尤德和麦若彬则首次参与谈判,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7]英方其他主要成员还包括英国驻华大使馆政务参赞高德年、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穆和港府派出的传译组首席翻译郑仰平,至于副政治顾问马德克亦曾署理麦若彬出席会谈。[8]会谈召开之初,尤德曾在香港的记者会上宣称自己是“以港督的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谈判”,结果被中方批评英国玩“三脚凳”的把戏,而且坚持不准有香港代表参与前途谈判,英方唯有在事后澄清尤德“当然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谈”。[7]
可是,第二轮谈判与第一轮谈判一样遇到重大分歧,其中,英方提出香港主权可于1997年后移交中国,但为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建议由英国保留治权,有关建议被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批评为无异于“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使谈判再度陷入困难。[9]面对谈判和香港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动摇,并引发信心危机。在1983年9月,港元兑美元汇率急跌,引发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现抢购白米等日用品的情况。港府为隐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跟美元挂勾,但中方则抨击英方是港元汇率急跌的幕后黑手,扬言如果一年内未能达成协议,就会单方面采取行动,自行在1997年前获得香港主权。[10]
由于英方代表团担心中方放弃谈判和单独采取行动,代表团在1983年11月成功说服戴卓尔夫人,放弃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在主权与治权上与香港维持任何关系,有关决定被不少评论视为英方的重大让步。[10]此后,中英谈判取得明显进展,双方确认了一些主要原则,当中包括香港在1997年由英国移交中国,中方在主权移交后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双方在过渡前后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以及让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国在1997年后维持某种不具居英权的关系等具体方针。[11]柯利达在1984年1月由伊文思爵士接任团长,而尤德和麦若彬继续留下参与谈判,但双方的谈判结果基本上已经定调,成为后来《中英联合声明》的基础。[12][7]
在1984年6月,中英双方设立两个工作小组就草拟《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文细节进行磋商,这两个小组由已改任助理国务次官的卫奕信为英方首席代表,并由麦若彬代表英方主理其中一个小组,负责国籍、居留权、民航航权和土地方面的条文,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内,两个小组以极速为《联合声明》定稿。[3]中英双方最终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并在同年12月19日由戴卓尔夫人和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正式签署。[11][13]可是,《中英联合声明》当时并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从民意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16受访者对《联合声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访者持保留态度,另有三成受访者认为《联合声明》提出的“一国两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对中英协议抱有怀疑。[14]
香港过渡期的风波
参见: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及六四事件

柯利达与麦若彬与中方召开秘密会谈,同意放弃由两局非官守议员制定的“两局共识方案”,有关行为被不少立法局议员批评为架空立法局和漠视香港民意。
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主权移交前13年的倒数,即所谓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麦若彬在1985年出任英国驻菲律宾大使,任内见证了菲律宾的民主运动与马可斯政权的终结。不过,麦若彬在菲律宾的任期并不长久,未几,港督尤德爵士在1986年12月死于任上,英政府遂于1987年改派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首席代表卫奕信接任港督,而曾经参与前途谈判、经验丰富的麦若彬,则获指派接替卫奕信出任英方首席代表,同时出任助理国务次官,负责亚太地区事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及其附件二,在1985年5月27日正式成立的组织,负责就《联合声明》的实施进行磋商,并讨论主权交接前后的过渡安排;小组需要每年在伦敦、北京或香港召开合共三次全体会议,每次历时四天。在英方首席代表任内,麦若彬定期与中方首席代表柯在铄举行会谈,但仍留在伦敦办公。后来应中方要求,中英双方在1988年先后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虽然柯在铄亦进驻香港办公,但麦若彬则选择继续留在伦敦,复于1989年派高德年为英方驻港首席代表。
然而,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并不完全顺利,并因为1989年的六四事件而受阻。在六四事件中,中共派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导致港人对香港前途陷入新一轮信心危机,更史无前例地触发百万人在中环集会示威,反映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中英谈判遂随着国际间杯葛中国而陷入困局。当时英国和香港有不少舆论呼吁英政府谴责和放弃《中英联合声明》,主流舆论更对香港主权将会移交中国感到忧心,当中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女爵士更公开恳求英国勿将其子民转让予一个“毫不犹疑地以坦克和武力镇压人民”的政权。与此同时,六四事件也激起港人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的诉求,在1989年5月,立法局和行政局的非官守议员达成了一致共识,推出“两局共识方案”,建议为香港代议政制改革立下时间表。根据方案,两局非官守议员均希望到1991年,立法局可以有20席议席(即总数的三分之一)由直选产生,直选议席到1995年增至一半,最后在2003年达至全面直选产生所有议席。
虽然“两局共识方案”获得普遍香港舆论支持,但却深受中方猜忌。在1989年9月,麦若彬与柯在铄在伦敦召开自六四事件以来的首个联合联络小组会议,令短暂中断的谈判重回正轨。同年年底,麦若彬随英揆外事顾问柯利达爵士秘密访问北京,就香港的政制发展进行游说,在谈判中,英方未有咨询两局的情况下,与中方达成了另一套协议。在麦若彬和柯利达提出的方案中,香港主权移交后的立法会在2007年之前,将有一半议席,即30席,由直选产生,在英方配合下,所有立法局在1997年前的改革将会先征求中方同意,以便香港立法局有所谓的“直通车”安排,能够在主权移交时顺利过渡到新的立法会。英方又有意设立“副港督”(Deupty Governor)一职,让将来的特区候任行政长官可在主权移交前作好准备。在这次秘密会谈意味中英双方放弃“两局共识方案”,而会谈中提及的立法会产生办法,后来则在1990年中方颁布的《基本法》附件二得到确认。[19]在1990年1月和2月间,中英两国外长再交换了七封外交密函,就1995年殖民地最后一次立法局选举如何衔接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达成秘密协议。
英国驻华大使
“玫瑰园计划”
参见:香港机场核心计划
六四事件后,为了振奋人心,港督卫奕信爵士在1989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宣布落实被港府誉为“玫瑰园计划”的香港机场核心计划。不过,由于计划造价昂贵,加上工程横越1997年,中方即时指责“玫瑰园计划”是一项企图要花光香港外汇储备的阴谋,并指这是英方秘密撤走资金的手段,表明不会“祝福”计划。麦若彬此时刚于1990年升任外交部副国务次官,并在1991年6月接替唐纳德爵士出任英国驻华大使,为设法取得中方表态支持兴建新建场,他上任后立即与柯利达又一次秘密会见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等人,企图为新机场一事“解话”,但中方坚持英揆马卓安要亲自来华签署谅解备忘,事件才可以完满解决。[柯利达和麦若彬与中方的秘密会谈,以及上一次秘密和中方达成协议放弃“两局共识方案”的决定曝光后,受到立法局多位议员批评,指秘密谈判的过程架空立法局,妨碍港人参与,其中立法局议员李柱铭更直言有关做法“换来一种剥削香港民主的制度”。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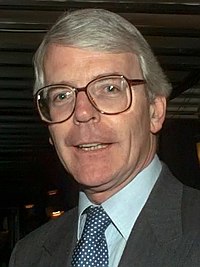
英揆马卓安不满卫奕信爵士和柯利达爵士对中方过份妥协。

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动“九五直选”,引来中方强烈不满。
柯利达与麦若彬秘密访华游说后,马卓安唯有答应中方要求,在1991年9月3日于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当中,英方承诺留予未来特区政府的储备将不少于250亿港元,换取中方支持新机场的建设,以及对香港主权移交后所剩下的举债问题采取积极态度。虽然马卓安表面上显得十分乐意到北京签署谅解备忘,但背后却对此十分恼怒,因为自六四之后,国际尚在杯葛中国之际,自己却被迫到那里签约,成为六四事件以后第一位到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此后,保守党政府认为对华的妥协政策已不适用,而马卓安认为对北京处处退让的卫奕信和柯利达要负上责任,两人结果在1992年先后被撤换,但麦若彬则获留任。
“九五直选”
卫奕信在1992年7月卸任后,港督一职由马卓安的党友、下院议员和政治家出身的彭定康继任。彭定康上任后不久,即对中方采取与前任截然不同的强硬作风。他在1992年10月发表《施政报告》,宣布在1995年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让全部议席透过普及的选举产生,以便加快香港民主进程,保障港人人权。有关决定虽然获得香港舆论和英国传媒普遍支持,但彭定康与中方却陷入相当恶劣的关系。在中方压力下,中英双方被迫公开在1990年初往还的七封外交密函,企图显示彭定康的方案有违中英双方较早前达成的秘密协议,但密函公开后,反而被立法局多位议员批评中英两国进行台底交易,不顾港人利益。
在1993年1月3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再公开反击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声称方案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既有共识,是“三违反”的方案,他扬言如果彭定康不放弃方案,中方将会“另起炉灶”,威胁取消立法局原有的“直通车”安排。为安抚中方的不满情绪,英方在1993年3月,宣布将与中方就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办法召开会谈,英方代表由麦若彬担任,成员则包括港府的宪制事务司施祖祥、港督彭定康的政治顾问欧威廉、副宪制事务司黎庆宁、以及外交部的李启思等人。不过,彭定康在同年3月12日向立法局宣布将政改草案刊宪,引来鲁平在3月17日于北京发表讲话,严厉批评彭定康将成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相方的激烈争拗,使会谈未开始便已经阴霾密布。
在1993年4月22日,麦若彬正式与中方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展开会谈。[27]双方此后一共召开十七轮会谈,至同年11月27日结束,其中麦若彬参与了首十四轮会谈。]双方虽然同意会谈建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双方已达成的既有共识,但会谈只能在一些横枝末节上达成共识,彭定康的政改核心部份始终未有触及。在7月和8月间,英方曾经向中方提交政改方案的修订建议,修订建议主要在功能组别议席和选举委员会议席的产生办法略作修改,但修订幅度基于会谈的保密性质,使外界无法知悉。不过在彭定康坚持下,麦若彬一方重申功能组别议席不可以以团体票选出,而且有份选出选举委员会议席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必须有充足的民意授权,这些重大分歧使到双方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此外,在会谈期间,英方宣布押后将政改草案送交立法局审议,激起立法局多位议员批评。在1993年5月26日的会议上,立法局议员张文光指责中英双方以会谈保密为理由,剥夺香港市民的知情权,令普罗大众对会谈进展一无所知,而麦若彬和姜恩柱也非港人选出,会谈上没有立法局代表,难以反映港人利益。
事实上,中英双方之所以愿意就1995年的立法局选举安排召开会谈,某程度上是要透过会谈各自博取香港舆论支持。虽然彭定康在会谈背后对英方施以重大影响力,但中方却坚拒彭定康参与,再加上双方分歧太大,以及中方的猜疑,使得会谈进程困难而缓慢,最后以失败告终,也导致中英关系的进一步倒退。会谈破裂后,政改方案的立法工作由港府在同年12月单方面重新推进。在1994年2月,英方和中方先后单方面公开1993年的谈判内容,其中,中国外交部更发表题为〈中英关于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会谈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真相〉的文章,企图将会谈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英方。虽然如此,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在1994年6月获立法局大比数通过,让他如期落实“九五直选”。此后,中方宣布放弃原有的“直通车”安排,并在1996年自行成立立场亲中和保守的临时立法会,而且声言不让殖民地的立法局过渡1997年7月1日,而原先“副港督”的安排也无疾而终。中英双方的恶劣关系,要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夕才逐渐改善过来。为表彰麦若彬在中英谈判所作的贡献,他早在1982年获英廷授予CMG勋衔,1991年再获KCMG勋衔,成为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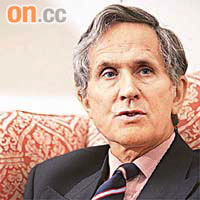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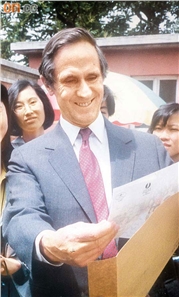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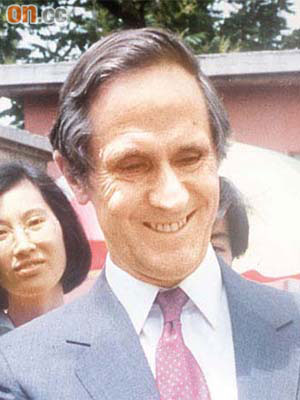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