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京夫
2008年10月07日09:25 陈彦
京夫走了,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们先后多次去看望,告别。
但真正意义上的告别,其实是在7月2日,那天我和贾平凹等一帮商洛老乡去家中看他,敲开门,夫人将他从内室扶出来,坐在一个硬木椅子上,同我们说了四十多分钟的话。虽然面容消瘦,身形枯槁,但尚有接待朋友的气力,并能看出来,他是尽量想撑着跟我们多说说话。为了活跃气氛,我们努力寻找着快乐的话题,说人生尴尬,说生活段子,更多的,说的是贾平凹在地震中损失的坛坛罐罐,以便引发贾平凹每念及此,就痛苦不堪的孩子般幼稚的表情。京夫一直没有说话,但他在听,在笑,在乐,虽然乐中难以掩饰那份生命的痛楚,可在一刹那间,也分明有忘却一切苦难的时候。这期间,还有两位朋友说没有他的长篇小说《鹿鸣》,他便让夫人取来,认认真真签了名。签名的书,在我们手中传递,字还是写得那么清正,疏朗,有力,甚至全然不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作家的手笔。
这以后,我就到北京出差了,一去就是半个月。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乡党们纷纷传播的短信:“京夫又一次住院,人已昏迷不醒,不久我们就将看到《八里情仇》的了结,听到最后一声《鹿鸣》……”这短信让人感到一种透心的凄凉。半个月过去了,我回到西安,急忙就去医院看望,这时的京夫,已是百事不知地瘫卧床上,白被单下,平摊着一架不用透视机就能看清所有轮廓的瘦骨,露出的双脚,萎蔫得已再不能支撑起大概不足五六十斤的身体,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在眼眶旋动起来。又过了两天,老乡贾平凹从外地回来,约我又去医院看了一次,境况更是大不如昨,平凹凑到床前,大声呼唤了几下,他已毫无知觉,惟氧气瓶在呼噜呼噜作响,一头白发映衬下的瘦削脸庞上,只突出着一双大睁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却再也不能洞见人世的友谊、亲情和悲欢离合了。
我与京夫相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十七八岁时,是一个文学青年,在家乡就见到了写《手杖》一举成名的京夫,他到镇安小县一个叫达仁河的地方深入生活,那个地方在“文革”中发生了一起叫“刘总司”的惊天大案,许多人死于非命,后来虽然得到平反昭雪,但好多家庭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他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作了好几本笔记,后来都陆续用在了作品中。我调到西安后,因是老乡,与他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京夫先生始终是个热情鼓励者,每有收获,他总是赞赏有加,呵护备至,有时说,有时就直接动笔加以褒奖,每每让我感到一种被提携和抬爱的暖意。我创作的几部舞台剧,他都悉心写过评论文章。因他过去也创作过戏剧,因而文章中总是传导出一种十分入行的心得,让人读后获益匪浅。再后来他从作协大院搬来“文艺家大厦”居住,我与他栖息在同一楼上,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时出去参加活动,总是一同进出,话题涉及面也越来越广。他的《鹿鸣》出版时,第一批寄来的样书就给了我一本,我很快读完后,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既是读后感,也是对他多年关心我创作的一种回敬。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有话想说。我始终觉得,《鹿鸣》是一部写得很扎实的书,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揭示的是十分深刻的,这种深刻、广博,以及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演绎出的奇异诡谲的生命变形样态,在我的阅读视阈内,尚不见更细密、雄图于此者,但愿在将来的某一天,《鹿鸣》会有另一番热闹景象,这当是后话了。在这部小说中,我甚至看到了与他年龄完全不相符的博大生命力,那种冲决一切的精神气度,让人咋都不相信这是一个即将走完全部生命历程的人的精神投射。但事实就是这样残酷,京夫先生的生命,在《鹿鸣》问世后不久,就将悄然终结了。
京夫准确离开人世间的时间是2008年8月3日13时30分。
他的心脏是在西安最普通的一家医院停止跳动的。
此时我正在午休,当醒来知道此事急忙赶往医院时,拉他的灵车已经驶出后门了。陈忠实和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正在灵车旁边,我走上车,想看看他,但此时那个暗红色的长匣子,已将他严严实实封存在了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了。车走了,我们站在医院后门外久久不知离去。这时,贾平凹也赶到了这里,大家便在一起说了半天京夫,太阳正红,晒得人的额头都在冒汗珠,但大家还都在说,以致全然忘了这是一个不适合说话的地方。
一个人就这样走了,我记得不足一年前,刚查出此病时,医院诊断是食道癌初期,“还算发现早”,京夫告诉大家时,还是从容、乐观的,但随着几次化疗,先是头发大量脱落,人也开始消瘦,再后来,体力就越发不支了。他从开始脱发起,就戴一顶灰白色的礼帽,帽子戴得很深,刚好露出眼睛,那眼睛就在帽檐的遮蔽中,显示出一种无奈甚至无助,每每看见这双眼睛,我就在想,历尽了人生磨难的瘦弱京夫,年逾六十又六后,是在品读着怎样一份深入骨髓的人生苦痛和孤独哇!
熟悉他的老乡都说:京夫一生几乎没过多少好日子。早先是大家都穷,他家比人家还穷,后来“文革”遭遇迫害,加之孩子又多,家口繁重,总是在艰难地往前“磨着”。文学本身就是最重的脑力和体力的双重劳动,自《手杖》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他的生命便被长篇小说《新女》《文化层》《八里情仇》《红娘》《鹿鸣》以及《娘》等诸多中短篇小说聚合成的四百余万字所攫取,躬耕劳作之艰辛态,可见一斑。京夫是以作品硬硬朗朗站立在文坛的,但却始终给人一种沉默寡言感,我老感觉他像书法的“瘦金体”,立得直,撑得硬,疏疏朗朗,干干净净,少了侵占其他面积的肥厚,多了“一杆独秀”的瘦硬精神。他为人谦和、冲淡,与他在一起,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种舒服有时甚至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他总是多说人好话,不议论人短长,哪怕自己受了很多委屈,说起“狠话”来也就那一句半句的,并且“杀伤力”极小。啥时他都是一种倾听的姿态,哪怕说者是幼稚得不能再幼稚的“妄言”,他都不会转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有时朋友聚会,都带了嘴来,说得唾沫四溅,他却始终只有一双耳朵在管用。我也见到他十分激动的时候,那是有一次说起一个黑砖窑圈禁“现代奴隶”的事,他竟然言语泼辣、不依不饶得嘴唇直抖动。那一天我突然觉得,这老汉要是活到八九十岁,拿一根手杖,瘦硬瘦硬地走出来,遇见不平了,也是会拿手杖对天对地乱戳几下的。
他终于没有活到那个需要用手杖的年龄就躺下了,近千人来向他送别,他的同道、朋友、作家晓雷先生,为他拟了这样一副挽联:“商州道中布衣粗食一根《手杖》行天下,长安城内锦心妙笔《八里情仇》撼人间。”京夫艰苦地来,又艰苦地去了。都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能对得住天地良心,亲人、朋友的好人,一个能对得住自己读者的“西京耕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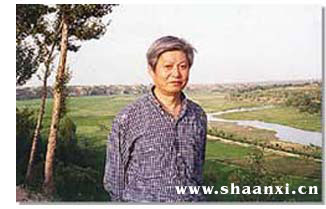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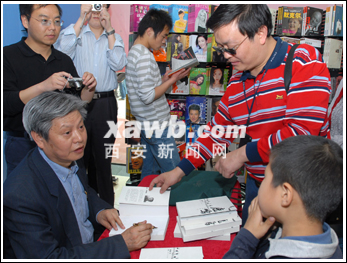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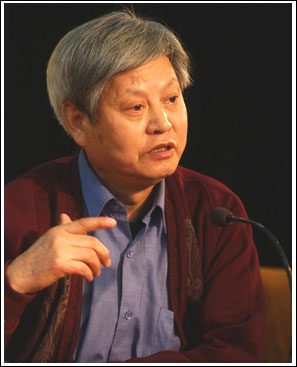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