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一)
在我的记忆中,从1938年至1946年这八年期间,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搬了六次家。这在解放前的北京,是个很普遍的现象。
1938年2月,我出生在北京市西城区小口袋胡同3号。这所小院子直到2000年,西城区公安局扩建时才被拆除。1954年至1956年,我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读高中时,几乎每天都要从这所院子门前经过。
不久,我们举家搬到和平门内后细瓦厂的八宝胡同(门牌记不清了)。这是一所前后两个院落的宅子。我们住在前院。后院(也是两院)住的是冯家。我们都叫他干爹。前院只有北房三间,东房一间是厨房,南面是满墙的爬墙虎,西面有一个月亮门通西院。弟弟纯正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记得在母亲坐月子期间,我们养的一只大公鸡,不知得了什么病死掉了,王大姑来家看望母亲和弟弟的时候,正赶上公鸡断气,大家都哭得很伤心。这只大公鸡遇到生人来家,会追着咬,专用嘴去啄生人的后脚跟,很厉害啦!当时是腊月天,天很冷,放了几天就冻了。后来还是把大公鸡炖了吃了。大公鸡很大,鸡肉满满一砂锅,端到桌子上,谁也不肯吃,围着一桌子的人又掉了眼泪。后来到底是吃了还是送给了冯家干爹就记不得了。
后来在这里还发生了一次偷盗事件,夜间贮藏室被撬开,丢了点儿东西,母亲决定搬家。
不久,我们举家搬到了后细瓦厂九号,离八宝胡同这个家只有三、四分钟的路程。新家的大门坐北朝南,高台阶。新家又是个前后院,我们住在前院九间南房。前院到后院只有
从后细瓦厂家出来向西走到胡同西口,路北是个水站。大皮带轮带动着抽水机,从地下打上来甘甜清凉的井水。当时,我已经在东绒线胡同小学上一年级了。每天中午上学时,总要喝点儿这又凉又甜的水。现在这个水厂早已关门了。
在这里又放生了一次偷盗事件。小偷躲在屋檐下,在月光下,窗户上便有个人影。住在前院西屋的男主人是个军人(记不得姓名了),马上朝人影开了一枪,小偷顿时被吓跑了。母亲决定再搬家。
从后细瓦厂又搬到了新平路。这是个坐北朝南的院子。我们住在南面的三间平房。这期间正值日本占领时期,父亲曾经带着全家去徐州修飞机场。我还记得在徐州的时候,我在河边的榆树上摞下来榆钱掺和在玉米面中蒸窝头。在徐州住了大概半年多才回到新平路的家。
不久,房东要卖房,我们举家又搬到了旧帘子胡同29号。这是所坐北朝南的前后院。我们住前院和后院的东、西房。后院的北房住着表叔陈汝辉、表婶
记得每到夏季,都请人来搭天棚。在天棚下摆上藤椅和茶桌,又喝茶又聊天,真是美极了!
在胡同洞口是个日本人的住所。门口有条大狼狗,还有日本兵站岗。每天上学总要从这里经过,总是提心吊胆。此外,在29号的东边不远的一颗大树下,总是趴着一直似醒非醒的大狗,有时从它身边经过时,它突然站起来,冲你“汪汪”叫。还扑过来咬你,你若跑,它追得更凶。每到这时,只好站住,大喊“妈……!”可是,妈妈哪里听得到,只要哭一阵子在慢慢挪着走回家。
在这个家里,我第一次请家庭教师给我补习作文。这位女教师姓樊。总是穿着一身旗袍,一条白色的手帕掖在腋下的袖口处。看上去也有三十多岁。人很和气。每次作文经过她修改后,让我背下来。我只记得老师改后的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改掉就是了!”我当时也不明白,这样的词句有什么惊人之处,以后作文也没有用上过!
在旧帘子胡同,让人最难忘的是家里养了一直老猫。由于老了,几天不吃不喝后死掉了。它生下了好几只小猫。老猫死后小猫一下子无依无靠,我和哥哥商量,把老猫埋在了胡同西边的一个小胡同里。这条小胡同出北口向西就是北京第三十一中的校门了(当时是崇德中学,是
在这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天空中经常轰鸣作响,据说是美国B51型轰炸机掠空而过。
日本刚投降,社会秩序不是很好。有一次,母亲去旧鼓楼大街大不桥看姥姥和舅爷。回来的时候刚到家门口,打开手皮包准备付钱的时候,后边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抢过钱包就骑车向西去了。从此,母亲决定再搬家。
母亲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家里的开支全靠母亲。我们兄弟三人每年收到的压岁钱,都让母亲积攒起来了。到了1946年竟然换了两根金条。
日本投降后,原红光电影院的经理想卖掉自己的住房,母亲看中了他在西长安街74号的一所小四合院。用两根金条买下了这所真正属于方家的宅子。从此,也结束了租房和搬家的历史。
我还记得第一次陪母亲去看房,请父亲的老朋友冯经理把小院子翻修一下。工人们从各个房间搬出来的都是日本的“榻榻米”。上面布满了臭虫。工人们只好把这些“榻榻米”搬到小胡同,用火烧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翻修,一所有十间房,包括北房三间,东房两间,西房两间,南房一间,东南房一间和西南房一间。小四合院的面貌焕然一新。水泥甬道直通院子各个角落,正房前面的花坛都漆了彩画。东、西房是平顶,前面都画了油彩画,绿色的门窗和窗纱,东、西房的窗板全是红色的,真是美极了!
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十年。直到1996年,我才从这里搬出。然而,这五十年又是不平凡的五十年啊!(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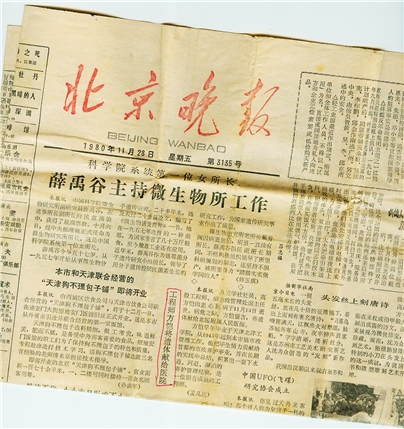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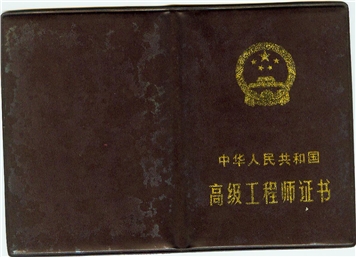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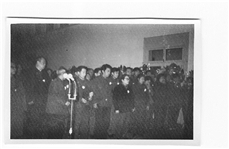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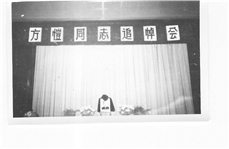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