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的方式
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
京报网 www.bjd.com.cn 日期:2006-10-17 网络编辑 : 张健
1.今年的世界性纪念
算起来,到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一百二十五周年的诞辰,十月十九日又是先生逝世七十周年的纪念日。关于鲁迅的纪念活动从年初就在各国开始了。先是日本仙台的鲁迅生平展,及东北大学的鲁迅医学笔记学术交流;接着有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鲁迅国际研讨会;九月七日,在香港举办的“鲁迅是谁”的图片展和“2006香港鲁迅论坛”,在声势上让当地的青年大开眼界,鲁迅风吹热了港岛内外。此外,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北师大、绍兴市、鲁迅博物馆及上海文化机构,已经和正在搞的相应活动不计其数。这些活动我参加了多个,印象颇深,每每有新的触动。当代世界文化潮流里的特殊的部分,因一位中国作家的存在而波动,在我们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前几日的香港之行,看到了那里的知识界的另一面貌。中文大学和香港图书中心的两场演讲,主要是港人。题目五花八门,从鲁迅与外国文学到国故整理,由诗学的阐释到儿童观,看法是很个体化的,有的内容之深,连内地的学者也佩服得很。比如李欧梵关于鲁迅与卡夫卡的讲演,就说出许多新鲜的话。王润华所谈世界汉学界的鲁迅研究成果,在思路上是别于他人的。黄子平探讨鲁迅文体上的个性,在精神的层面有闪亮的地方。没有料到讲演的专家那么多,许多非文学专业和非现代文学专业的人也加入了进来。少见陈词,多为独思,据说那些文章要结集出版的,当然会激起读者的兴趣,我对此深信不疑。
沈钧儒在鲁迅葬礼上演讲
2.民国时期的自发纪念
七十年来,鲁迅的纪念可谓多矣。上海上万人的送葬仪式,延安鲁艺的创作活动,北平左翼作家的地下出版,及港澳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纪念刊物的问世,都书写了思想史不凡的一页。历史上纪念鲁迅的方式有许多种,集会演讲,戏剧演出,实物展览,学术交流,样式翻新。看到民国年间一些纪念活动,着实为那一代人的真诚所感染。萧军、张仃曾搞过一次活动,一张由张仃画的巨幅鲁迅画像,忧患的目光十分传神。(许多年后我采访张仃时,他对我说自己去延安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那是鲁迅祭日到来的时候,青年们自愿地组织起来的活动,是为了追溯一个伟大的灵魂。现在已不知有多少人参观过那幅画,我们从历史的旧迹里还是可以触摸昨日的余温。从那时人们的艺术讨论,以及有关《呐喊》、《彷徨》的争论,是可以发现激进思潮的轨迹的。
1936年鲁迅之死在文坛引起的反响是不同寻常的。我在博物馆里找到的一些资料,大出意料,媒体的反应之大,在现代史上是少见的。现在人们谈鲁迅,总说他是被政党文化捧起来的。这是不懂历史的缘故。1937年,上海波文书局出版了《鲁迅纪念集》,含有极多新闻和悼念文字。总的印象是民间个体的活动多,自发的纪念四面开花。上海、北平、香港的文化界的反响,不是今人可以想象的。比如香港《大众日报》曾刊发“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征文启事”,其中写道:
噩耗传来,文坛的巨人、民族革命的斗士鲁迅先生溘然长逝了。这在中国,在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中,失掉了一些什么,那是完全不可估计的。
我们为着纪念他领导文化界为大众自由,为民族解放的热忱和毅力,特刊发“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希望同声哀的人们踊跃投稿。
远在北平的文化人,在那一年也有许多的集会。连鲁迅当年的宿敌也表示参加相应的纪念。《民声报》刊有“故都文化界扩大追悼鲁迅,由个人团体双方发起”的标题。消息说:
个人方面由曹靖华、许寿裳、沈兼士、顾颉刚、朱自清、谢冰心、沈从文、孙席珍、梁实秋等发起;团体方面由作家协会,北方文艺社,世界语编译社,学生联合会,妇女救国会等发起。
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文人在那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茅盾、巴金、曹禺、萧军的文字和谈话后来经常被人们所引用。当年攻击过鲁迅的郭沫若,态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上海文化报》记载了留日同学会追悼鲁迅的情形。郭沫若自己说是以徒孙辈的身份参加此会的。遥想当年,他化名麦克昂的笔名亵渎鲁迅,能见出世风之变。文人之间是怕对比的。一对比就高低具现。郭沫若的先抑后扬,是真实的转变。诗人气质在那个年代,是随时风的变化而变化的。像郭沫若这样的人物,在心底佩服鲁迅,文化界的基本倾向则一目了然的。民国的文人自负者、狂妄者比比皆是。鲁迅一逝,使他们看出自己的孱弱。桀骜不驯的陈独秀,笑傲江湖的钱玄同,都著文夸赞逝者的高贵。在黑暗到极点的时代,鲁迅的有无,实在是不一样的。
鲁迅死前曾希望人们忘记自己,不要搞纪念的活动。但他却获得了一般人少有的荣誉。人们追思他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1936年之后,每年秋天都有与鲁迅纪念相关的文字问世,电影、戏剧、研究文章和展览,在文化界从未中断过。孙犁在战争中,不顾条件的艰苦,写鲁迅的故事寄托情思。丁聪以漫画的形式,复原《阿Q正传》的内蕴。内山完造几乎把后半生的经历用于鲁迅的宣传普及里。十几年前认识画家裘沙夫妇,他们一辈子在做和鲁迅相关的艺术活动。像茅盾、郭沫若、巴金的纪念文字,都可以编出许多书来。这个现象和普希金死后极为相似。人们在这个丰沛的遗产里发现了诸多永恒的存在。至少那些精神的律动,把麻木的世界激活了。
宋庆龄和姚克在葬礼上
3.为什么要纪念鲁迅?
为什么要纪念鲁迅?除了文革中的荒诞的仪式外,在许多地方是真挚的追思。人们想于此寻找今日缺少的存在。无论是智性还是趣味,是学识还是见识,可以与鲁迅比肩者不是很多。有一年闻一多先生出席悼念鲁迅的会议,公开向先生道歉,认为自己当年骂鲁迅是错的,因为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人生观上,鲁迅的文字写出了世界的本真。闻一多早年喜欢纯净的艺术,是唯美派的。在书斋里看云听雨,是悠哉游哉的事情。可置身于社会的激流里,感受则完全不同了。大凡走在泥土里和风雨间的人,往往觉得与书本世界的不同。鲁迅不属于书本的世界。他的思想跳跃着,是尘世里的歌哭,搅动着地下的岩浆,散出的是生命的热力。在没有个体的人的混沌世界里,他呈现了个性的张力。在没有希望的地方,他以抗争而闪现出弱小者的希望。他用燃烧的心灵之火,驱走了身上的鬼气和阴郁,予人以温情和爱。所以,我们看那些纪念鲁迅的人,似乎是一种心的寄托,有的近乎宗教的情结。虽然大家知道鲁迅讨厌个人崇拜,不希望人们记住自己,但由于他把世间不曾有的东西呈现给了世人,纪念便成了自我的寻找和光明的追随。一百年来的作家有此魅力者,唯此一人。
4.大江健三郎们的感怀
友人高远东私下和我说过一句话:中国文化中,有两种传统是有原点的意义的,它们至今还影响着现代进程。一是儒家的传统,二是鲁迅的精神。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就后者来说,能激起那么多人与当代的问题对话,说明我们今天的文化依然存在着一个类似五四时的难题。鲁迅的意义在于触及了这些难题,且把文化的一种可能呈现出来了。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在直面当下难题的时候,往往发现鲁迅的资源的可能性。亚洲好的作家在这点上差不多都在认可鲁迅。了解这些,便能体味人类的一种深切的渴念。
大江健三郎谈到东亚的困惑时,首先提到了鲁迅资源的价值和他对自己的影响。那种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及在没有希望中寻找希望的搏击精神,正是人们需要的存在。许多年来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感怀鲁迅,日本知识界的举动也意味深长。在东京、仙台、福井,经常有关于鲁迅的活动。仙台的东北大学近来排演了话剧《远火——鲁迅与仙台》。编剧是位经济学家,演员有老师、学生和职员。我前不久到那里看他们的演出,很是感动,没有想到剧本写得那么精致,演员也颇卖力气。这个剧团是长年演出的,默默传播着这位中国文豪的思想。东北大学近来还组织了科研小组,专门研究鲁迅的医学笔记。参与研究的人有搞经济学的,有医学专家,还有文字学教授。为什么那么执著地思考鲁迅,这在日本知识界是一个现象。用大江健三郎的话说,鲁迅比日本的作家高明,也比许多思想家高明。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远古我们有一个孔夫子,现在有一个鲁迅。文化的新生,是从这样世界意义的思想家那里开始的。我们现在还在这样一个传统里。
谁也说不清七十年来关于鲁迅的纪念会召开了多少,论著早已汗牛充栋了,现在又到了先生的祭日。也许社会上的活动还有许许多多吧。在这样的时候,郑重的表达有时会流于形式,当纪念仅变成仪式的时候,那离我们的怀念者是遥远的。钱理群先生说过一段话,对鲁迅最好的纪念是读先生的著作。这是对的。默默地与一个灵魂对话,充实我们的枯燥的心,比什么都要重要。
作者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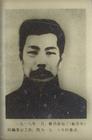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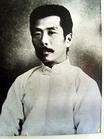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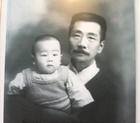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