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去地坛
“师傅,去地坛。”
天坛、颐和园那么赫赫有名。他说:“来北京几年了,我还真没去过天坛。”车开
到半路,又打开我提供的地图查看:“应该离这儿不远。”的哥厚道又负责,绕了
些路,得多付些车资,我也不怪罪他。
就是为了专来拜访你。当然,我可以请求熟识你的友人介绍,提上几样洋礼登门拜
访你,叙谈文学合影留念。但那不是我的方式,平生,我最怕的就是打扰人,尤其
是文人忙人,还有病人。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上门定会打扰你一天的平静、思考
和写作,还有休息,那将是世间最罪过的事情。
皇,色泽以宝石蓝和朱红为主,飞龙延柱祥云飘端,花费看上去少不了。好是好,
就是少了古朴少了阅历少了味道。二三十个民工打地铺睡在露天的水泥台子上,盖
着家乡带来的花棉被,赤着脚丫,脏垢着头发,还没有“起床。”他们如此赶工,
想来也是为了迎接一个月后将盛开的奥运会。京城里这几年天翻地覆,将旧貌换成
新颜,都是为了这个盛会。
人。我想,你是听见了,看见我了。当然,你并不认识我,我只是你素不相识的读
者,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我只是按图索骥,因读你的<<我与地坛>>而来这里拜访
你。
的居民,几乎看不到我这样兴致勃勃东张西望的访客。我走在中间的人行道上,以
便观赏“两岸风景”,有人在慢慢悠悠地打太极拳,有人在提着鸟笼子溜鸟,还有
人在京胡的伴奏下吊嗓子,咿咿呀呀,十足的京味儿,几个老人家高谈阔论着将召
开的奥运会,互不相让。显然,眼前的地坛早已不是你笔下的地坛,是近年政府投
资重新修建过的,笔直宽阔的大道,平坦整洁的小径,每隔七八步的垃圾箱回收箱,
浇灌打理得让人看着舒心的草地,不时出现“小草怕疼,脚下留情。”的牌子,也
就跟着卖起票收起钱来。不知你是否喜欢这里的变化呢?我只是知道,已不是你的
地坛,你笔下的地坛。
你这样描述这里,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也就不会向往来到这里。
一个二十岁的下乡返城知识青年,一夜厄运突降,下肢瘫痪,过早失去父亲,只有
收入微薄的母亲陪伴着你寻医求医,什么专家什么权威,什么偏方什么“祖传秘方”
半仙都看过了试过了,可是你的腿还是像木头做的,不听使唤,站都站不起来,别说走、跑、跳、
蹦了。命运这个混帐王八蛋最后的裁决却是:“小伙子,你将终身残疾。”
梦幻?多少理想多少抱负?你爱穿上心爱的回力球鞋跑步,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爱借来邻居老八的拍子打乒乓球,打得个个残败,叫你是“壮老二”;(壮则敦是第
一)爱和几个哥们踢足球,用力一脚,球儿冲上半天空。又多爱瞒着母亲,骑自行车
出城偷偷在水库里钓两条草鱼回来,让母亲为全家滚一锅鲜美的鱼汤。多爱写几段
小诗,跑去“她家”,鼓足勇气塞给她,“今天晚上地坛西门见,我等你......”
你知道,她也对你有意思,就是还没戳破那层纸......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你说。
恨不得被车撞死被雷霹亡。每天你都逃离人群逃离喧闹,你都到这里来,早晨、黑
夜、晴天、雨日、春暖、冬寒。推动着轮椅,有时是沉默地安静地出门,有时是焦
躁地怒不可遏地“咣!”打开门,头也不回地冲出家,如冲出笼子的疯狗,那轮子
的声音就是你的怒吼和叫喊。留下你浑身颤栗心如刀剜泪水早已干枯的母亲,可怜
的女人,她站立在那里,雕塑一般,动也不动,心里重复着:“我的儿呀,我的儿
呀,千万千万不要......,你就是瘫在床上了,还有妈陪着你。”
你的眼睛被园子盛满着,你的身体被园子拥抱着慰藉着安抚着,就如婴儿时期在母
亲安全温暖的怀抱里。那徐徐的风,是母亲的喘息;那阻拦你的树枝,是母亲拍抚
你的手;那热得令人出汗的太阳,是母亲亲手纳的棉被;那遥挂天空的星星,是母
亲凝望你的眼睛。那时这里是都市里的村庄,无人管理,树木野花都是野生野长自
生自灭,原始而质朴。无人打扫的树叶果实,经过风雨的侵蚀腐烂风化,变成了肥
料,营养着大树灌木。片片荒草任枯任荣,春来泛绿秋来断枝。那时的路都是行人
蹋踩出来的黄土小路,定是窄些坎坷些,却能看见脚印,让人猜路过的人穿的什么
鞋,是大人还是小孩,是迈着大步还是走着小碎步。那时人们刚对付着吃饱肚子,
绝无溜小长毛狗的妇人,也无滑旱冰的孩子。有的是小贼眼睛滴溜溜望望你,又飞
速逃过,消失在草丛中的野兔。还有梧桐树枝上啾啾唧唧鸣唱,和你作伴儿的鸟儿。
也许,那时你难以接受将终生以轮椅代步的现实,嫉妒小鸟都有可飞翔的翅膀,游
翱天空,想落在哪儿就落在哪儿,忍不住骂一句:“滚,去你妈的。”鸟儿受惊飞
去了又飞回来,因为它们要给你唱歌和跳舞,善良的鸟儿愿意逗一个落难的人开心,
更想看到你那怕短暂的笑容。
我为什么来到人世?该不该去死?还是苟且活着?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活着?......几
年间,你每天到这里来,从早到晚都是问自己这些问题,这些健康的人有工作的人
繁忙的人顾不上自问的“蠢问题”。你在这个园子里走呀走呀,不是,是手不停地
推呀推呀,让两只轮子碾过这里每一棵树的树影,碾过每一米草地。更多的时候,
你就坐在或半趟在轮椅上发呆,苦思冥想着什么,又似乎脑际一片空白。寻寻觅觅,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答案?多少次,你扭头看见在远处焦急张望来寻找你
的母亲,你装着没有看见她,待她看见你后她又静悄悄地离开了。有一回,她又来
找久不回家的你,她视力不好,怎么也找不到你,你坐在矮小的树丛中,看着她,
看她从你的身边经过,去别处寻找,你却没有喊:“妈!”你为什么决意不喊一声?
你后来说那也许是长大男孩的害羞和倔强,我却猜想,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已让你精神崩溃,如溺淹苦海不能自拔,一点
顾上体谅母亲的感受。看到母亲和你一样终日惜惶受苦受煎,你也许产生了一些报
复和发泄的快感。你埋怨母亲带你来,却让你受苦受难,连路都不能用脚用腿走。
那活着还叫个人吗?
孤单单天天都到这儿来的小伙子。”我仰头问路边一棵棵茁壮茂盛的银杏树,它的
叶子比较奇怪,像把小小的扇子,树的枝桠上缀满了青青的果子,有手指头那么大。
到了秋天就可以吃了,据说银杏的叶子也能当茶泡来喝呢,防止老年痴呆。我想你
也曾俯身捡过落果,又抛向远处,消磨无聊的时间,制造些动静看自己还是不是活
着。我止步凝望着枝头一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鲜红的,有着黑丝绒似的尾巴,可
称鸟中的美鸟。我不敢走不敢动,甚至不敢呼吸,怕惊动了她,怕她展翅而去。当
年,你是不是也是坐在轮椅上,眼睛眨都不敢眨一下地看着这只鸟的老祖奶奶在银
杏树上梳妆打扮,歌吟曼舞,和你对视。它看着你,用圆溜溜亮晶晶的一对小眼睛
看着你。它的叫声多动听呀?它长得多逗人喜爱呀?某一天的某一刻,像被围困的
蚂蚁终于找到了出口,你豁然开朗,你在心里狂叫着:“我要活着!我要活着!”
活着,起码能看见蓝色的天,让小雨打在的脸上;活着,起码能让寒风刮在头顶,
让雪花降落到手掌上;活着,就能到这个园子里来“走”......
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就是怎么活的问题了。”这就是你用七、八年时间苦苦思
想,在这园子里找到的答案。
跑,求了爷爷告奶奶也找不下一份工作,“研究研究”就没了音讯。你自学过外语,
又放弃。后来在街道小工厂和一群老妈妈们画过七年彩蛋,一月薪水三十元,仅够
维生。那些个年你不是孤独而来,而是携书而来,买来的、借来的、朋友送的、母
亲找来的。和你同来的还有笔记本和钢笔,心里有些东西就渐渐涌上来,逼迫着你
要写下来。你找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唰唰唰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没有构思没有斟酌
没有开始没有结尾没有顺序没有主题,更没有想会不会发表,会不会引起评论家的
关注。多年的积累在一刻决堤,表达的欲望在一刻爆发。思想到哪儿笔就跟随到哪
儿,纸上的笔在飞,纸上的字在飞,你的思绪你的情感你的精神,甚至你不能行走
的肉体都飞向另一个世界......洁净的、空灵的、超越凡尘的......
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
诞生地成长地。
地时的响亮宣言,更没有人捧上鲜花和礼物。是地坛的寂静拯救了你,是地坛的古
松拯救了你,更是写作拯救了你,是文学拯救了你。你终于明白:“只是因为我活
着,我才不得不写。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是的,你说
的话一点没错,“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从此,有一样东西让
你日夜牵挂,让你时时琢磨,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痛苦,却怎么也不舍得丢弃,舍不
得早早地结束自己。因为你还没有写够还没有写完还没有写出最好的,还要写要写
......
你这
字对陶冶情感净化心灵有着巨大的作用我不否认,我还要说:写作能拯救人,写作
曾拯救我。在我人生道路上两次出现感情和精神危机,患严重忧郁症,几度想尝试
自杀,濒临绝境时,都是在绝望之中抓住一根文字的稻草,把内心的忧伤和苦闷倾
吐出来,挣扎着游向岸边,伴随着读书写作,再次重生,再次上路。我想,如果人
世间没有文学没有写作,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有时,我猜测,上帝只所以不同
意让我那么早去天堂报到,是让我“你写点什么吧,急什么?”虽然,我的写作对
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微不足道,但起码让我不再那么自卑,不认为自己是个一无所用
的人。我沉缅其中享受其中,这就足够了。那怕读者只有我一个,我也要写。
一根能撑扶自己的拐杖。那是要自己去苦苦寻找的,我侥幸地找到了。
也爱运动爱打扮了,皮肤也变得细腻滑溜了。整个人变得愉快变得有活力变得充满
自信。
水从心底涌出流淌,一点一点浇灌滋润着干枯久旱无心经营的心田。洗刷出灰暗尘
埃藏垢垃圾,托运去伤痛忧郁自卑自哀,随着一行行字落下,随着一篇篇文章完成,
我重新翻梨耕种的土地渐渐张出了新芽,生出了嫩叶,打上了花骨嘟,种栽出一片
红娇绿翠的心灵花园。写作,拯救了我的身心,让我重新变成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
珍爱自己的女人。
写作真是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摘自我的散文<<心药>>,我喻写作为疗心之药。
你也会这么说。热爱写作的人,是任何地位钱财名誉都不愿意交换的。写作,哪里
是为做别人的灵魂工程师,有时,仅仅是为了安顿自己疲惫受伤无所适从又的身心,
对自己有个交待而已。
有了文字,你有了漂泊人生苦海上的一只帆船。有了写作,你有了一味支撑你决心
活下去的良药。有书读,清苦艰辛的日子也过得富足香甜,每有新作,受病痛摧残
的肉体也得到莫大慰藉。有了些成绩和名气后,你时常自责悔恨,母亲在年纪轻轻,
仅四十九岁时就患肝癌去世了。没有看到你呕心沥血日夜笔耕变成铅字的作品,她
没有看到你荣获大奖,名扬文坛的一天。你说:“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
就召她回去。”其实,要我说,母亲去世了,但她还是和你在一起。你每一次来这
里,她都是尾随着你来的,只是她站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走她走,你停他停,
像时候学习走路一样,她跟着你,怕你摔跤,她又距离你远远的,是为了让你
自己大些胆子走,走远些。你看书时,她在你的身后看着你,提醒你:“傻儿子,
歇会儿。”你写作时,她也是默默地陪伴着你,在微微地笑,在偷偷地抹去眼角的
泪水。“终于,儿子找到了他喜欢做的事情,好好写。”当夜晚来临,写作修改一
天了的你,呼呼入眠发出酣声,母亲又会来看望你,轻轻抚摸你消瘦的脸,她曾经
多次按摩敷药的腿。母亲会在灯下一页页阅读你的大作,即便是草稿废稿,母亲也
会说:“你写得多好呀。可不能扔了。”你的点滴成绩你的巨大成功,你的母亲都
知道,她会以你为荣以你为傲。你不必过于自责,那样母亲也会难过的。你听见了
嘛?我们的亲人不在了,可还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他们住在我们的心里,一直陪伴
着我们。
上笑得如盛开的花朵,灿烂照人。她身边是个大脑袋,憨里憨气,成天嚷嚷着要吃
糖果四五岁的你。谁能看出这个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呢?你说过:“我
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是的,面对一个二十岁陡然残
疾的儿子,唯一的儿子,从没有乞求过他一句:“你也要为我想想。”她晓得,儿
子已经够苦了,够绝望的了。她能做的是帮助儿子收拾好轮椅,打开门,目送你远
去,让你独处,让你安静,让你自己挣扎,让你为自己找出一条路来。她见你几小
时不回家时,又心焦步乱地来这
焦急慌张?找到你,又只是远远地看着你,怕打扰你,怕你又发脾气,怕你又埋怨
人尊敬爱戴的母亲,也是受苦受难最多的母亲。如果你不嫌弃,也让我和你一起叫
她一声“妈妈!”我真希望和她一起来寻找你的,还有我,那样她是不是就不会那
么孤立无援那么六神无主那么惊恐担忧?我真希望,我能牵着她的手一起来,帮她
踩到脚下的野草,拨开繁密的树枝。我的眼神好,会很快找到你。那么我们的妈妈
就不会受那么长时间的煎熬。当她疲惫无力时,让我搀扶着她回家,给她做碗热挂
面汤。当她又垂泪难过时,让我轻轻地拭去她的眼泪。我们的母亲已哭的太多太多。
边眼镜,简朴的衣衫,你总是这个样子。你正面向我走来,我侧过身,让你的轮椅
从容地经过,你微笑着摆摆手对我说:“谢谢。”我答:“走好。”我多么想蹲在
你的椅前和你叙谈,可是不敢打扰你,也许你要回家写作,也许到了要上医院的时
间。你的背影停顿在树林深处,你是在看渐升的太阳还是闲步的游云?你就长时间
地停顿在那里,你在我眼中就是一副思想者的画像,安静、深邃而永隽。你在埋头
愤笔激书,唯恐刹那间光顾的灵感又毫不留情地溜的不见踪影。写作绝对是勤快人
干的活儿,正吃着饭要放下饭碗写下一句半言,半夜起夜想到什么也要赶紧记下下。
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今生能看到你的文字,走进你的内心,到这里
看望你拜访你。
原来在我陕西富平乡下老屋的门前,父亲种的绒线树,既是你母亲从郊外挖回来小
苗,栽在小院里慢慢地长大、开花的合欢树了。即是在异国他乡,每回从那家门口
有棵绒线树的人家走过,我都放慢脚步抬头仰望,心里默默对你说:“这就是你写
过的合欢树,你看见了嘛?花开得可好了,数不清有多少朵,像粉云缭绕在树上,
清雅得很呀。”这种树的花比较罕见,不是一瓣瓣组成,而是许多根麦芒似的花针
组成花朵,不艳不咋,自有一番韵味,朴素如乡下的女子。很早以前,你种合欢树
的母亲走了。几年前,我种绒线树的父亲也走了。你说你写作的动机有巨大的成分
是:“为了母亲,为了让她感到骄傲。”我在自己的散文集第一页上写到:“献给
父亲。”没有他们这一代人苦难艰辛劳累血泪的人生,哪有我们作品的份量和价值?
虽然眼前是新的草坪,整齐翠绿,但你曾在这里静坐思考,这里有你遗留下的气息。
我和你素不相识,我只是你千万读者中普普通通的一个,走在这个你来过无数次的
园子,你脱胎换骨重生一次的园子,你曾阅读写作的园子,就如同见到了你。我的
泪水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盈满眼眶,不停地吸溜着鼻子,得拿出纸巾揩擦,别人会以
为我有什么伤心事。今天,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多情的人,是个爱流眼泪的人,常
为一篇文章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小细节一副感人的摄影流泪。但这眼泪不是悲悯不是
同情,而是感动。被你的经历感动,被你的文字感动,被你丰娆、深刻而又纯洁的灵魂感动。被你平凡的母亲感动。
冲刷着我们内心天长日久积淀的尘土脏垢,清洁着我们日渐老花浑浊世俗不堪的眼
睛。眼泪是给眼睛洗澡的液体,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明亮单纯真城......
一下。我找到一张油漆已经斑驳脱落的长木椅,请一位晨练的路人为我留影。左边
的位置空着,我想像你就坐我的身旁,脸上还是戴着那副宽大的眼镜儿,开怀大笑
着,露出整齐的牙。看过你的几张照片,几乎都是笑着的,从没有见哪副是思想家
作家模样,神情凝重拿着笔吓死人。虽然已五十好几的你身体虚弱不堪,每隔一天
都要去医院做肾透析,药物反应也让你体力不支,长期的坐卧让你生出褥疮......可
是这三十多年,你唯一做的,就是写作写作写作......你早已留下了话“该走的时
候,我就走。请不要救我。”
在轻轻地走,一点一点的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轻轻地走,一点一点地走,
我们都是同路人。只是漫漫长路上要留下自己的脚印,哪怕是轮椅的痕迹,洒下自
己的文字,让她们变成花草,露出自己的笑容......还要潇洒地自嘲:我不写作,
我死了拿什么做枕头?
好好活着。活者,我们第一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
旅游景点,又地处奥运中心不远,当然要修要建要挖要改变了。你只能无可奈何地
说:“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我已不再地坛,
地坛在我。”当然,在我们的国家,国家利益首都形象奥运会“绿色和谐”重于一
切。但是,我还是愿意愚蠢地设想,如果在一个因为主人不愿意砍伐一棵老树而让
高速公路改道的国家;在一个几十辆车为野鸭过街停住,耐心等候,他们中不乏
“高干”“贵族”的国家;一个为一名先天智障老人在重建区保留下他工作一辈子
的破旧咖啡馆的国家;如果一个敬重作家尊重个人权力的国家;也许,这个城市的
市长看过<<我与地坛>>后,也被你感动,他会和城建小组商议,为你保留下往日的
地坛,为我们保留下旧的地坛。一个城市少了一个相似的公园,却拥有着一个文化
思想者生命留痕的圣地。它告诉访客:“我们保留这里的原貌,是为一名作家,他
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骄傲。”他至少应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有人会嘲笑我是白痴,
那就笑吧。
的总是好的,旧的总要被毁掉被代替?我想我是日渐老去了,越来越怀恋珍惜旧物
旧景旧地了.....
愚不可及,甚至荒唐的问题。“如果,假如,可能,人的命运能够选择,能够操纵,
你要做一个从二十岁青春年华起就终身以轮椅为伴的伟大的杰出的作家,为人类创
造出丰富的有分量的宝贵的精神食粮,还是要做一个身体健康,能走路跑步,上班
买菜,做家务陪儿子踢球伴妻子逛商店的平凡男人?我知道我知道,无论是哪个答
案都过于残忍,都不是人说的话。可我又忍不住一次次问自己,我要哪一个你?作
家的你?健康的你?当然我希望能够两者合一,那是最完美无缺的答案。但是上帝
有那些痛不欲生的体验,没有在地坛里的挣扎搏击,没有这里的安静抚慰,就没有
今天的你,没有那些作品。既便你是作家也是另一个作家。那我们读者的损失可就
没法计算了,只有老天爷晓得了。
双十年华上就突然残疾,是你最大的不幸,绝处逢生,以写作支撑苦难的生命,而
且你有天赋有才华,又是你最大的福气。人只看见金子的光泽和价值,没有看到矿
石在火炉中的翻滚和锻炼;人只看见玻璃柜台里珍珠的圆润和美色,哪里知道蚌中
心疼磨合的时时刻刻;人只品尝到白沙糖的滋甜,哪里知道那甘蔗为此粉身碎骨奉
献一切。还有,你在陕北放过牛,你知道牛黄是怎么产生的嘛?我务农一辈子的父
亲说,是牛生了病,产生出的一种东西,慢慢长出来的。牛病得越厉害,牛黄就越
大,牛也就越疼痛......
哄赶牛,那是生产队的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可耽搁不得。你回来就一病不起,
最终不能走路。你就是那么赔上性命长出牛黄的耕牛嘛?牛黄有价,听说比黄金还
昂贵,你的文字哪能用人民币计算?它是你苦难的结晶生命的结晶,是你以终生的病痛不能行走换
回的“牛黄。”让我对你深深鞠躬,说一句:“感谢你。”感谢你让作家这个名称
在这个商业金钱时代依然神圣依然洁净,依然让人由衷地尊敬,而不是与排行榜销
售量轰动效应挂钩。也让我对地坛深深鞠躬,说一句:“感谢谢你。”感谢你和他
同喜同悲,陪伴他安慰他激励他走过那些黑暗的岁岁月月,看着他成为一个完整的
人,超越的人。
回的“牛黄。”让我对你深深鞠躬,说一句:“感谢你。”感谢你让作家这个名称
在这个商业金钱时代依然神圣依然洁净,依然让人由衷地尊敬,而不是与排行榜销
售量轰动效应挂钩。也让我对地坛深深鞠躬,说一句:“感谢谢你。”感谢你和他
同喜同悲,陪伴他安慰他激励他走过那些黑暗的岁岁月月,看着他成为一个完整的
人,超越的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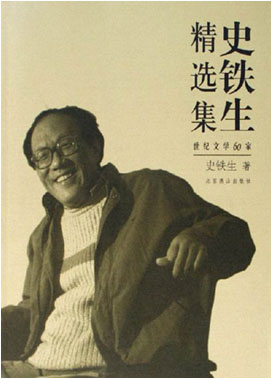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