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沈培新会长
怀念沈培新会长
安徽省公安厅 陈加胜
“沈会长走了。”
“走了?”我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想。
“昨下晚去世的!”
“……?”我不能再疑问了。
其实,沈培新会长患病、住院的情况我一直在关注着。期间他住院、出院、上班,断断续续的。当月我还两次去过他家看望他,他虽然消瘦很多,但精神还不错。特别是不久前他在省新四军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时,精神依然矍铄,我幻想着他能够挺过这一劫!
不久,我听说他又住院了。我正准备去医院看他时,意外地接到他打到我家的电话,显示的号码是他家里的电话,证明他又出院了。
他说:“桂建平同志要我组织几个人再写一本书,我写了个框架设想,已由会里邮递给你了,你有什么意见可直接在上面修改。”他停顿一会接着说:“我想请你参加这本书的编写,你重点写新四军在皖南的三年,你看怎样?”我为了他的健康,这次我没推辞了,满口答应了他。
我拿到他起草的“框架设想”后,认真思考了几天,正准备去向他汇报时,谁知接到了崔纬国这样的电话,我敬爱的沈会长还是被无情的病魔带走了。
接崔纬国电话后,我即请假直奔沈会长家,他家挤满了很多人,都是去吊唁的,我没看到灵堂,打听才知,他身前有过“后事不要俗套,不要设灵堂,不要送花圈,不要开追悼会”的遗嘱。
他,一直奉献、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实在是太累了!
一、我认识了沈培新会长
第一次见到沈培新会长,是送《新四军军史》书稿。这里,我还得先啰嗦一下我为什么写《新四军军史》:
我出生在当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乡罗里村,叶挺、项英当年就曾居住、工作在我们村,距我家没有几步路。小时候听到很多有关新四军的故事,从童年懂事起就对新四军有着仰慕之心。
由于当年毛泽东主席对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袁国平等全盘否定,加之文革中刘少奇又被打倒,故当年新四军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几乎埋没,家乡父老乡亲们对此鸣不平,打那时起,我就有了“长大要把新四军历史写成书”的志愿。
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后,我考上了安徽省公安学校,毕业分配到省公安厅一直从事刑侦工作,利用奔跑在全国各地侦办大要案件的工作之余,走访了一些老新四军,靠工作之暇的零星时间零打碎敲,于1989年底完成了30多万字的书稿,后因忙于业务工作无暇顾及,一直搁浅15年。
2005年得知我省还有个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我想,自己业务繁忙,根本没时间研究新四军历史,就决定把书稿送给研究会。
我找了几个大学生帮我的手写稿打成文字,分章装订成9本,通过安徽省徽派文化传播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行水,去到省委小花园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王光宇会长家,得到白忠宝秘书的热情接待。
王光宇会长接见了我,肯定和鼓励着我,并指示我把书稿先拿到会里看看。我即去找到主持省新四军研究会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会长沈培新,沈收下书稿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后,说他先看看书稿后再联系我。记得那是2005年8月24日。
大约20多天后,沈培新会长约我到他家里,当时我拉着李行水董事长一道去的。我原打算把书稿送给省新四军研究会,希冀为研究新四军历史工作者作参考,也就结束了。然而在王光宇、沈培新等领导们的关怀和器重下,情况发生了变化。
沈会长这次见我时说,他看了我的全部稿件,总体不错。随之指出不足,提出希望。最主要的是,他说这是作者个人的心血,要以我个人名义出版这本书,这是我意外的收获!为圆我童年时的志愿,我就没舍得谦让了。
为了使更多的老新四军和军史研究人员、学者能够有针对性地修正我的书稿,我决定先印刷出来分发给他们。为此,王光宇会长亲自给我题写了“新四军军史”书名。特别是沈培新会长给我写了《序言》,还帮助我联系了印刷厂。李行水董事长的公司义务为我排版、申报书号,崔纬国主任帮我设计书的封面。我的第一本《新四军军史》书就这样出版了。
二、他是照亮我的举灯人
记得我认识沈会长不到一个月时间,省新四军研究会准备写一部反映新四军故事的《走近新四军》专题片和书,为此在省委专门召开了“新四军历史专家咨询会”,沈会长特地邀请我去参加。我到会见有十几个人在一个小会议室,都是生面孔。沈会长介绍我认识了负责编写剧本和拍摄专题片的安徽电子音像出版社编辑部崔纬国主任和孔令春女士,崔主任手里拿着我的手写稿问:“陈老师,这是您写的吧?”我知道他是在高抬我,更明白沈会长将手写稿交给他们的意图。沈会长叫他们编写时参考我的材料,其实更重要的是想我尽快地进入角色,给我创造人缘、环境等方面的条件。
我受宠地坐上了位子,按说我没资格坐那儿,更没资格去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可我想既然从单位请假来参会了,况且还拿到和与会者一样的300元劳务费,在沈会长引导下,我还真的班门弄斧地说了起来。记得我讲到“1940年秋日军万余人打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其中一路5000人打到云岭了,是叶挺携曾希圣指挥云岭至泾县战场的,曾希圣成了参谋长的角色……”话没讲完就被一党史专家打断:“你讲错了!是周子昆随叶挺指挥的,不是曾希圣……”我停下等他讲完后又说:“我原也是这么认为的,周子昆是军部副参谋长嘛!可我查阅史料是刚到新四军不久的曾希圣。周子昆参谋长也上战场了,他率部在南陵方向阻击另一路日军,他和叶挺不在一块……”我没敢再继续辩论下去,我清楚自己在新四军历史研究方面充其量是个业余爱好者。这时主持人沈会长讲话了,他的一番讲话,我现在想不起来他的原话了,但总的感觉是,他的讲话是在一种平和而低调的语气中婉转、和蔼地圆场,使我又能体面地继续坐在位子上,也使对方能宽容我。
从此以后,在沈会长关怀下,省新四军研究会的许多活动他都通知我参加,只要是节假日或业务工作能抽开身时我都去参加。我认识了很多老新四军和党史、军史工作者,搜集到了许多史料,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我几乎耗尽我的所有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于2007年底编著完成了一本76万字的反映新四军全部历程的《我所知道的新四军》。
书稿完成后准备出版发行,我先通过北京的朋友们联系上了军科院和解放军出版社,在多次的电话洽谈后,又去了北京一趟,效果不佳,主要是经费问题。书号、审稿费和去一趟北京的食宿、请人吃饭等等费用都要自理,我没这样的经济基础,无奈地被迫放弃了。
不久得知这一情况的沈会长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去一趟北京,要我把书稿复制一份给他带去,并介绍我认识了省地质印刷厂的朱蕾(铁军书画社副秘书长)。沈会长在北京找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后来我电话与这位领导多次联系,两个月后这位领导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看了我的书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给我宣传讲了一些出版这类书的政策规定,一是党史军史类的书,严格地说个人是不能出版的;二是即使要出版,书中的一些内容和照片尽管是史实,也要拿掉。我不愿删掉这些内容,也没时间再去作更大的修改,没精力去奔波交涉了,就婉言谢绝了,因我繁忙的业务工作已容不得我继续耗下去了。
一段时间后,我在沈会长、崔纬国主任、朱蕾秘书长等同志的关心下,此书终于在合工大出版社排版、在省地质印刷厂印刷,于2008年7月出版了。
《新四军军史》、《我所知道的新四军》先后出版后,沈会长、崔纬国主任考虑出版费用都是我个人出资的,故帮我推销了许多,省新四军研究会还给我颁发了个人三等奖。在我没能够参加的省新四军研究会召开的学术委员会研讨会上,省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徐则浩在报告中用了较长一段文字表扬了我,很多与会者将此情况电话告知我,我上网查阅了徐则浩会长的报告,觉得过奖了,我只能将其作为鞭策。
一系列的活动,使我增加了对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的热情,渐进地改变了我的原计划。我原计划退休后,结合自己几十年公安侦查工作的实践,专心致意地研究公安侦查业务,况且我已在公安部、中国刑警学院、公安大学、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刊物上发表过50多篇公安侦查业务论文,经常在中国刑警学院等院校和全国、全省公安业务培训班作这方面的专题讲座和授课。记得1993年我受中国刑警学院的指派,在沈阳给编写《中国刑警》电视片剧本的作家和全体剧组人员作了一场《刑警的酸甜苦辣》的报告,反响很好。可这时我想放弃此计划,准备退休后去省新四军研究会上班,专门研究新四军历史。此计划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沈会长的关爱和引导。
2006年我向沈会长表白了我想参加新四军研究会这个组织,也为在研究新四军历史、发表文章时能够名正言顺。他即答应我“等换届选举时考虑”。随即我就有关历史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错杀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史实真相、还“皖南事变”几个历史问题的史实真相等等。
我记得在2007年9月的一天,我在江南出差,有朋友电告我说,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正在筹备召开第五届换届会议,我即打电话给沈会长表白我要参加研究会组织,他爽快地答应我:“欢迎你,担任理事或常务理事都可以。”我说:“我单位工作忙,出差多。担任理事就足够了。”11月6日会议召开的那天我去参会了,我果真被提名理事,也被选举通过了。
2008年下半年,沈会长告诉我,会里准备编写一本“皖南事变”的书,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因业务工作担子重,怕没这个精力,就绕开了这个话题。
我不能再不知趣了,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皖南新四军从离开云岭开始,在茂林与国民党顽军作战的全部过程”和“军部首长及各部队分散突围的全部过程”的两章内容。
在沈会长的主持下,58万字的《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于2010年8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了,并得到中央一些重量级的党史、军史研究专家们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一些重量级的军史专家还为此书撰写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我曾两次与沈会长谈心时说,写这个内容的书,开始我很担心易“炒冷饭”,即使出版了也很难有什么影响力。没想到却有了如此之大的社会效果。编写和发行此书的过程,我确实领略了沈会长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方法的艺术性。
记得2011年底,有人告诉我,说研究会准备提名你担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学术委员会开会的头一天,有位副会长在研究会通知我参加会议时就说了:“陈加胜,你要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呐!明天的会不能迟到啊。”
第二天我去参加了会议,由于路上堵车,我还真的迟到了。我看到的会议材料上对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提名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领导同志。我自然不会言语的,也不会去打听缘故,切不可成为引起是非之人。再说我还在职,繁忙的业务也难使我胜任。
这件事却使我联想到了一些现象,和我住公安厅并同楼同门栋、原是我所在的刑警总队政治协理员齐振藩,他在上老年大学,沈培新会长是他们的校长。一次碰到我说:“陈加胜,沈培新校长对你的印象很好……我与他交谈过你的情况。”又一次他碰到我说:“今天我去省新四军研究会看望沈培新校长了,他对我说:‘陈加胜退休后就到研究会上班,就坐我这个位子。’”我听了也就听了,没去多想。但总感到沈会长关切的温暖,时时在吸引着我。
事后,我隐隐约约地听说,当时在研究选派哪10个同志去参会时并没有我,后来是沈会长与中国新四军研究会联系增加了1个名额,说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馆长的那个名额不在我省10个名额之内,但必须推荐一个“热爱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并有一定成果的年轻同志”。
我是9月5日中午到南京的,当时我省其他代表还没到。大会筹备处通知我参加了下午的筹备会。晚饭前,我省桂建平、王海瞳、王传厚等领导都到会了,来自全国各省(市、区)会议代表约270多人,大会分成4个小组。没想到,我被大会确定为大会第一组联络员,每个组有两个联络员,第一组的另一名联络员是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将军张光东,他是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小儿子。当时,我觉得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太器重我了,我怎么能与张光东将军平起平坐了呢!
在当晚全体代表预备会上,通过举手的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会议议程、会议分组及各组召集人和联络员名单。这次会议我被提名并通过选举成为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这些都是沈会长这位举灯人照亮我的结果。
三、怀念沈培新会长
沈会长走了近两年了,但我没觉得他已经走了,他讲话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我发现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他在大家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的离去,且是一种深切的怀念!印证了诗人臧克家那句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沈会长就属于后一种人。
在与他认识后的短短几年中,不能说我与他共事了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多少时间,因我属于那种“开会时才到、散会就走了”的人,但他的为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看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是摸之不去的。
我是个“未老先衰、用脑过度、两次从死神那里逃生”的人,都是因业务工作超负荷运转、身体透支而导致的。故今提笔写此文,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却一时难理出个头绪来,只能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了。
一是他的人缘好、朋友多。记得我在出版第一本《新四军军史》书时,必须先取得书号。李行水、崔纬国等同志都在帮我忙,李行水董事长还安排他公司的人陪同我去合肥市政府政务区窗口申办书号,可办得很不顺利,没成功。
后来我带司机又去政务区,我索性撇开窗口、直接闯入出版局版权处,进入处长办公室,毛遂自荐后,就汇报自己申请个书号、准备出书的事,并把书样递给处长看。当他看到沈会长写的《序言》时说:“沈培新会长原也是我等的领导,后虽不在一个系统了,但他一直在关心爱护着我们,他是个好人。”这位处长亲自帮我办理,指导我填写了表格,带我见了局长,并获得局长的批字。因他们还得找专家审稿,我交了审稿费就回去等通知了。没多久,书号就批给我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碰上一个沈会长的熟人,竟然有如此大的效果。
我在出版第二本《我所知道的新四军》书时,通过关系找到合工大出版社编辑部朱移山主任,他帮我申报立项、修改书稿、直到排版。这时还需要总编审再次审稿把关,可他工作特别忙,迟迟摆不上他的办公桌(审阅76万字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当他得知是沈会长作的“序言”时,立即连班加夜地修改我的书稿。他说:“沈培新会长德高望重、口碑很好,大家都尊敬他!”这又是我意外之收获!
二是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社会。自从认识沈会长后,我出差在外地有时也给他打个电话,发现他会议、活动很多。后来我逐渐知道,他不仅在省新四军研究会担任执行会长,他还是省老年大学校长、老年大学协会会长、省铁军书画社社长、省文联主席、省哲学应用学会会长、省文艺发展基金会会长,以及在省陶行知研究会、省徐悲鸿教育基金会、省教育学会、省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省人才学会、省行为科学学会、省战略学会等等组织担任领导职务,他还是省委党校、安徽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沈会长出身于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他父亲抗战前就参加革命的,一直在北京工作。他的兄长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一直在浙江省工作。记得他还告诉过我,他家族里有好几个人参加了新四军。在他身上有一种潜移默化、传承下来的革命优良素质和作风。在他患了绝症,稍好一些就出院上班忙工作。当他病发卧床不起也不忘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一天,他还在病床上为研究会的一些工作与有关方面通电话、召集有关人员到他病床前布置具体工作任务,组织文化、新闻、理论界知名人士举办一次论坛会,策划活动的安排……他确实是一个“退而不休”的典范!
三是他的文笔功底很深。刚认识沈会长时,我只知道他当过省教育厅厅长、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文联主席等领导职务,对我来说他可是个大领导了,大领导的讲话稿一般多是秘书写的,我不知道他自己的文笔如何。不久,他给我编著的《新四军军史》写“序言”时的情况,令我难忘。
他给我写“序言”时,要我先替他写,我在家认真地写了1000多字送给他,他说:“我先看看,看好后再交给你。”我回去后想,最少也得个把星期的时间。没想到当日下午他就叫我把稿子取了回来。他没重写,是在我的稿子上修改的,内容几乎没改动我的,但文字语气全改了,80%的文字都修改了,而字数仍然保持在1000多字,我顿时对他肃然起敬!不仅是因他这么快就把稿子修改完并交给了我,而是80%的修改面,要换成我,还不如重写呢!可他没这么做。他如此的辛苦,不仅尊重、鼓励着我,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高我的文字写作水平,使我能够直观地看到如何使文字表达水平提高档次、变换角度和变换口气来表达。记得我在排版校对期间,拿着样书又去过他家一趟,他看了看“序言”后,又问了些我工作经历情况,当即提笔在“序言”后又加了一段:“在我们不断的交谈中,我感到他是个兢业务实、勤奋好学的人,对事业忠心耿耿。他心系国安,情系民意,立志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而努力。他不为升官而围绕官场转,他不为金钱而围绕钱场转,而为人民转战江淮,留下他平凡而深深的脚印。”
后来我在朋友们面前谈论此事时才知道,沈会长文笔功底很深,他不仅主编过很多报告文学和专著,还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发表过200多万字的文章,筹划拍摄过一批影片和电视片。
四是他不应该走的这么早。沈培新会长是青阳县人,18岁入党、20岁参加工作,先后在合肥师范学院、省人事厅、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工作,80年代初就是省教育厅副厅长了。他关心人、乐于助人,我在新四军研究会、铁军书画社圈圈里常常能听到一些同志在念叨他的好处,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较强的亲和力。正如有的同志说的:“他与同事、下级相处始终亲和。”他是个“宽厚的长者”,是一位有思想、有才华、有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水平的人。他不仅文笔好,口才也好。这些年我常常看他在大小会议上讲话,他的讲话没有什么套话、大话、空话,而是言简意赅,时有新意。
我与沈会长交往的几年中,点点滴滴,记忆犹新。他才76岁,不应该走的这么早,太可惜了!这么好的领导,若能更加长寿,继续和我们在一起,那将是何等的幸福!
我记得他曾经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人活百岁不是梦》,介绍他自己生活的经验,讲了很多修身养性的哲理,鼓励老同志愉快生活,加强锻炼、科学饮食,以赢得健康长寿。可他自己却过早地离开了,是造化弄人吗?我想,他工作上的劳累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身兼那么多的社会职务,排队等着的会议、活动,毕竟是奔80岁的人了,工作时常在一种透支状态,更谈不上“按时锻炼、科学饮食、规律生活”了。
敬爱的沈培新会长,我忠心地祝愿您在那边的天堂能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写于2014年2月8日
备 注:
作者陈加胜,现任安徽省公安厅督查专员。
系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安徽省大别山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合肥市新四军研究会军史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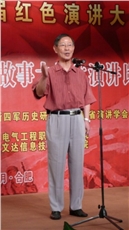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