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怀念王钧
10月18日,王钧去世。19日晚,南方都市报记者张艳芬电话采访了我1个小时20分钟。今天是王钧的追悼会,我不能抵达现场,送她最后一程,特将和张艳芬的通话整理出来,以此小文怀念王钧,以及我们曾经共有的纯真年代,光辉岁月,乌托邦。
问:你和王钧共事多久?
答:18年前,南都即将创办日报,我们是最早的一批招聘编辑记者。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办,我去了北京,她留在广州。
问:那时的王钧是什么样子?
答:正,真,拼。简单,干净,直接。有理想,有锋芒,有灵气。风风火火,敢想敢干,相信我能。也难免青涩,粗粝,冲动。王钧的这些性格,正是早期的南都性格。
问:后来的王钧有什么变化吗?
答:稳健了,宽容了,策略了,精细了,专业了,价值观更加明晰坚定了。
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答:年龄大了,阅历多了,变化是自然的。从一线记者到中高层管理者,角色的转变必然有新的要求。南都18年来的风风雨雨,更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所有人。与其说王钧变化了,不如说南都变化了。王钧的变化体现着南都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初心不改。
问:你作为王钧曾经的上级,对她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答:放心。王钧做事情,从来不会偷懒,不会不动脑子,不会掉链子。如果做不成,做不好,一定是客观原因,其他人更做不成,做不好。
问:王钧有什么缺点?
答:我想不出来。这并不是为死者讳,而是我觉得王钧所有可能的缺点,比如因为对事不对人的耿直而遭遇的意见,都是上述这些金子般的优点的另一面,不重要,更无法苛求。
问:听说当年提拔王钧时有争议。
答:这不稀奇。想干事,想创新,想怒放,想坚持点底线,想坚持点情怀,不甘于无趣和平庸,争议是必然的。南都当年吸纳了一批牛鬼蛇神,个个有争议。我被提拔时也有争议,庄慎之龚晓跃张晓舟,随口一列,哪个没有争议?甚至程益中喻华峰也从来没有完全逃脱争议。
但南都对人的争议,从来不在业务层面,仅限于莫须有的性格方面。稿件版面业绩,众目睽睽,谁也玩不了假。每个人都是靠真本事吃饭,靠裙带和资历混是混不下去的。至于性格,每个人都受益于被包容,同时也明白包容别人的可贵。
南都作为一个媒体,18年来也一直饱受争议。人如其报,报如其人。无争议,不南都。
无论是人还是报纸,小节有瑕,大节不亏。就是这些有争议的人,成就了唯一的南都。就是这份有争议的报纸,成就了一群闪光的人。
问:怎么评价王钧对南都的贡献?
答:作为记者的王钧,总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猛料。珠江新城还是一片久未开工的荒地时,王钧就独家拿到了整体规划,我编辑了一个整版。
地方新闻是地方报纸的立报之基。初创时的南都,社会新闻一枝独秀,有黄色小报的特征。要想主流,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时政新闻来源。当时的政府部门看不起南都,眼里只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好像今日的互联网,言必只称BAT。在影响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突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优秀记者个人。王钧和其他时政记者刘庆孙雪冬邱小红等,硬生生撕开了这个缺口,让南都的新闻水准上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台阶。
南都从来不愿意只当体制的传声筒,从来就视监督公权力为天生的责任,这样就和政府部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程益中概括为“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南都的代价,多出于此,南都的荣誉,也多出于此。王钧从时政记者转为主管时政新闻的部门主任,到后期成为全面主管广州新闻和珠三角新闻的编委和副总编辑,在她的职责范围内,成功拿捏了这个分寸,包括2003年一系列针对SARS的著名报道。建设南都最重要的板块区域新闻,王钧作用重大。
另外,传承南都一以贯之的文化,发掘培养了一大批好的编辑记者,也是王钧经常被感念的地方。
问:我就是王钧招聘进来的。你能回忆一个关于王钧的细节吗?
答:2005年下半年我到广州出差,王钧夏逸陶王景春等陪我一起在海印桥的一家KTV唱歌。喝了一些酒,王钧说杨斌我们跳个舞吧。我笨,绊倒了她,两人同时倒地。坐在地上,王钧大笑,站起来时,王钧泪流满面。
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答:王钧是公认的性情中人。我们没有问她原因,我们也不需要问她原因。一言难尽的快乐和感伤,得到和失去,都在我们心里,懂。
问:你后来还见过她吗?
答:见过多次。我昨天翻到了王钧的一篇微博,记录了2012年4月22日我们的见面。我知道了她的病情,抱着见最后一面的想法,去她家里看望。
王钧喜欢古诗词,我送了两本书,蒋勋刚刚出的《说唐诗》《说宋词》。我太太窦婉茹也是南都前同事,她让我带去了一束花,提醒我要在来得及的时候表达心意。我们在小区里散步了一个多小时,王钧写道:“绿树都已参天,安静自由地生长”,“理想依然在,不止笑谈间”,“没有什么放不下,经历着就是生活着。”
问:你们谈到了生死吗?
答:我们没有回避这个话题。王钧对生有留恋,对死不困扰。跟她的冲淡达观相比,我内心隐藏的沉重显得多余。
问:那次见面有什么感受?
答:云淡风轻。
王钧说,知道并治疗病情这么长时间,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反过来都是她在宽慰家人和朋友。王钧酒后经常哭的呀。但当真正的挑战来临时,却没有一点期期艾艾。无论在她的微博和微信,还是当面深谈,你都看不出来她是一个癌症病人,以致于我有一种错觉,也许她的病没有那么重,也许她就是创造奇迹的个案。
我猜想,在人生最后时刻,王钧大概也会平和一笑,给活着的人以力量吧。
问:知道她去世的消息,你的反应是什么?
答:我和王钧同龄,同时进入南都。1996年底到2003年间亲密共事了7年,见证了南都一路向上。那是我们共有的纯真年代,光辉岁月,乌托邦。过去和人相关,构成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相关的人死去,就好像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
问:大家都很难过,你也知道现在的报纸困境。能说一句积极的话吗?
答:南都刚创刊时,程益中就说:“南方都市报印的不是报纸,是人。”新京报创刊大会上,程益中又说,多年以后,“落英缤纷”。你看,程益中的预言正在实现。
人会死去,报纸也会死去,但是过去并不因为死去而不存在,生命并不因为死去而虚无。人和报纸曾经散发出的光亮和热量,仍然会绵延传递到更广阔的时空,生生不息。
王钧说过“向死而生”,这也算是另一种解读吧。
杨斌
2014年10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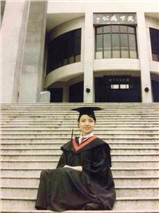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