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黑龙江历史名人、爱国者于浣非二三事
记黑龙江历史名人、爱国者于浣非二三事
为纪念 “九一八”事变七十六周年
一、 于浣非的父母及弟妹。
于浣非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没有文化知识的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十来岁随祖父从河北北上闯关东,在松花江边落户后,拜师学得一门手艺,成家后就靠编制柳条包挣钱养家糊口。母親的娘家也是从山东逃荒至松花江边的,她也是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
于浣非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两个弟弟和五个妹妹。他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决心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们读书。靠借贷供于浣非读书,他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当小学老师,他的学生中有的年龄比他还大,个子比他还高。就这样,他半工半读,从初中到高中,直到从哈尔滨医专毕业。
医专毕业的同年,为寻求爱国救国之路,于浣非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推行新三民主义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並为其贯彻一生。这期间他还从事兴办文艺,推广新文化运动,撰写和创作了许多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各门类的文学作品。
他的弟弟和妹妹靠自身的努力,分别进入哈工大和中等医护专门学校,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抗日爱国行动,对弟妹们的爱国意识和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于浣非的父親病逝于哈尔滨;一九六一年,于浣非的母親病逝于台湾。
二、离开哈尔滨去北平。
一九三二年哈尔滨沦陷后,于浣非仍在哈尔滨,他在同记商场、大罗新百货商场任医药部主任,并兼任以上两商场及同记工厂的广告部主任。並与陈元福,[陈钟,建国后曾在长春市任职,文革后在吉林省任职,]于炳然等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中共地下党员苏敏[建国后曾在铁道部任职]在哈生病期间,住在于浣非家中十数日,于为其治病并常陪伴其在松花江边散步。
于浣非在哈尔滨的抗日活动,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监视,在他为抗日义勇军筹集运送医药用品之后,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搜捕,在先到北平的同学赵惜梦及同学张末元夫妇的帮助和接应下,于一九三四年初,与老母和三个年幼的儿子转移去北平。
不久后,被迫转移去親戚家躲藏的妻子[李相云,又名李劍寒]和不满周岁的女儿,在于浣非的弟、妹的帮助下,也去了北平。
之后,于浣非的小弟也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参加抗日军队而去。妻女到北平刚安顿好,于浣非和赵惜梦就离开北平去了武汉。
三、于浣非在武汉。
一九三五年初,于浣非又将妻子儿女迁往汉口,与赵惜梦等人同住在一幢楼里。
于浣非在北平和到汉口初这段时期,以親身经历和流亡见闻,用朴实无华的东北语气,写出一出短剧<鞭子>。为了推出此剧,他邀约东北的流亡爱国人士排演此剧,並亲自上街头演出,饰演用鞭子逼女儿卖唱的老汉。此剧试演后不久,有几位年轻人士来到于浣非在汉口的住处,索看了该剧本手稿,並经作者本人同意将手稿带走。后来被谁人发表,己无从查证,但此剧成为火爆一时的抗日街头名剧是不争的事实。
于浣非不计较名利,只要对抗战有好处,谁去发表都没关系。从他以后的历程也足以证实。他一生从青年时撰写文稿,創办文学刋物,以及武汉时期及四川成都时期所写的大量文稿、演讲稿,到离开大陆时为止,他没有整理保存,以作为将来获取名利的筹码。
在他去世之时,也仅将晚年的几部著作,刻在墓碑之上。
于浣非又以佚名为笔名发表诗歌<我在中国生,我在中国长>,此诗被收入<爱国诗集>,并被他人谱曲传唱。此后,为了自身的安全,于浣非多以佚名发表作品。这也足以证实,他只求能唤起民众,对抗击日本侵略者多做一些实事,不想成名成家。这也是他的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与敌人斗争的策略性。
他用过不少笔名,其中有:濯清、淖清、浣非、于飞、宇飞、眠石、于宇飞、佚名……等等。
于浣非在汉口与赵惜梦一起创办由张学良出资兴办的<大光报>,兼任经理、广告编辑和撰稿人。从延安来武汉创办<新华日报>的刘利锋(音),就住在于浣非家中,据说他是延安派到<新华日报>的第一位党代表。[刘利锋是于浣非在哈尔滨时期支助的孤儿,並成为朋友]。<新华日报>印刷厂与于浣非在大路里的家相距仅二、三十步。不久后,刘利锋的妻子领着两个孩子来到汉口,仍住在于浣非的家中。他们朝夕相处,两人的妻子、子女成为好朋友。
这期间于浣非还常去上海、山东、西安等地从事采编和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战争暴发前,于毅夫等人在武汉发起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于浣非积极响应,並成为主要骨干。他的家人和妹妹(及家人)都加入了东北救亡总会。同年,为筹集办报经费,于浣非专程去了西安,在他返回武汉的两三天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西安事变”。
<大光报>停办后,为了生计,于浣非又找到一份武汉海关卫生檢役的工作。这时,早在哈尔滨就己熟识的肖军、肖红也来到武汉,于浣非通过文化界的朋友,帮助他们安顿下来。
于浣非的最小的妹妹这时也加入共产党並前往延安。
抗日爱国志士豈文彬受伤后,来到武汉养伤,住在于浣非的家中,直到伤愈。
在武汉期间,于浣非夫妻支持鼓励年幼的儿子和侄儿参加抗日儿童演出队,年仅十岁的大儿子还自编自演剧目,到医院慰问受伤的抗日将士。武汉沦陷之前,一九三八年六月,于浣非加入战时保育院疏散沦陷区难童的工作。
于浣非的大妹(于汝洲)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挚友,是战时救助难童保育工作的重要骨干。他的大妹、二妹(于淖汶)都是医生,她们都全力以赴参加了这项工作,还冒着危险到即将沦陷的战区,去收集难童转移到武汉。
难童急需往后方转移,于浣非担任第十三批难童的随队教师和医生(另外还有两位已有身孕的女教员),这批难童的年龄在五到十五岁之间。他的妻子儿子都参与对几十个难童日常生活的管理。从汉口出发,五天到达宜昌。在宜昌等待换船,等了两个多月。于浣非的二妹带领的第二十二批难童,也到达宜昌。在等船的日子,还将子女和难童组成歌咏队,在宜昌街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于浣非还在街头作抗日宣传演讲。
一九三八年九月到达重庆。同船到达重庆的赵惜梦全家,南下去了昆明。另两位女教员因临近产期而辞职。
于浣非一行再换乘两辆軍车,又忍受了两天两夜的颠簸,最终把这批难童平安送到四川成都,移交给设在成都皇城内的保育院。
而在几年的流亡途中,于浣非自己和他妹妹们一共失去了四个年幼的孩子。他们都是因为生病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和治疗而夭折的。
四、于浣非在成都。
在武汉出世的第四个儿子在到达成都几个月后病逝。一九三九年,于浣非发起在成都的东北藉文学艺术界同仁,在祠堂街少城公园对面的新又新电影院,举办了纪念苏俄文学家高尔基逝世三周年活动,以示对红色苏联的敬意和对中共抗日主张的支持。这也是于浣非一生坚持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治纲领行动的体现。纪念会场悬挂的高尔基像,就是于浣非画的。
流亡到成都的东北藉爱国人士,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于浣非是分会负责人之一。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的联络地点设在成都市东胜街沙利文舞厅,不久发现有陌生人常来窥探,怀疑是国民党的特务,为安全起见,将会址转移到于浣非家中。
于炳然在成都期间,也在于浣非的家中住过几日。在四川成都期间,于浣非开办过医院,先后担任过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健康教育督导队的督导员,省政府秘书室卫生视察员。他经常到四川省各州县,及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巡视医疗活动,为学校学生、穷苦百姓及少数民族百姓治病。
于浣非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薪水,远不能养活一家七、八口人。他的妻子則承担起养儿育女的主要责任,在成都开办了一家牙粉公司,制售牙粉、癣药水、雪花膏、鞋粉等维持生计,于浣非为其产品设计广告和商标。
于浣非妻子经营的牙粉公司,为支援抗战,在一九四四年搞了一次在西城一带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奖学义卖活动,将收入捐献给抗日军队。
又冒着政治风险,受委托以其牙粉公司名义作担保[铺保],把被关押在成都市国民党的监狱里的中共地下党员袁志杰[音。女]营救出来,袁出狱后,住在于浣非的家中休养有月余,直到取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后赴延安。[建国后袁曾在北京市任职。建国初期,審干运动中,李相云为她证实了这段历史]。
日寇飞机轰炸成都后,于浣非参与四川和成都省市文艺界举办的,揭露控诉日寇轰炸成都暴行的大型画展,继续进行唤起民众抗日的活动。他的不满十岁的三儿子也到被轰炸现场,写生作画参展。他的几个孩子和妹妹、朋友的孩子还组成歌詠队,到大街上作抗日宣传演唱,于浣非也到街头作抗日演讲。
这期间于浣非又创作了另一个反映在沦陷区的中国妇女抗日杀敌故事的剧本<大红鞋>。该剧本的篇幅长短与<鞭子>相当,语言风格与<鞭子>极其相似。
此期间,赵惜梦先后在昆明、兰州等地办报低,于浣非受聘担任他的报纸的特派记者。在成都期间,于浣非经常出入他的四妹在祠堂街开的书店,在书店楼上写作。书店吸引来许多东北藉流亡爱国人士,受到街对面 “努力歺”歺厅老板,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的注意[车时任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车耀先主动与于浣非交往並成为朋友。
于浣非的孩子们还应车耀先之邀,去参加他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大声社”的活动。车耀先还为于浣非的大妹妹的儿子安排就读在成都较有名气 的中学。肖军夫妇到成都后,与于浣非家来往密切,并将一幅鲁迅親笔书写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条幅,赠予于浣非夫妇。肖军尊称于浣非夫妇为“大哥”、 “大嫂”,而于浣非夫妇则昵称肖军为 “黑小伙”。
肖军、王德芬夫妇去延安前夕,将不能随身携带的许多书籍、<八月乡村>印刷纸版、一本由肖红本人写的日记、及一张方桌{在桌子底下写有 ‘肖王’二字}等物品,寄放在于浣非的家中。此后失去联系,肖军夫妇一直没有去于家取物。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于浣非的妻子李相云一直默默地支持着他的抗日救亡爱国活动,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作出无私的奉献。所有与于浣非交往密切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都能感受到李相云对他们的敬重和无为不至的关爱,所以,他们都把李相云尊敬为自己的嫂子。
五、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于浣非断言:国民政府太腐败,未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居住成都期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不久,于浣非的几个妹妹、妹夫及家人聚在一起,议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于浣非曾向他的几位妹妹及妹夫表明自己的看法:“国民政府太腐败,未来的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
抗战胜利,为尽快回到东北,于浣非离开成都去重庆,得到国民政府委任的东北救急总署卫生署付署长之职。返成都几天后即去东北长春上任。将他的妻子和五个子女遗留在了成都。不久后,其母以及大妹、二妹等也离开成都去北平。于浣非在长春没呆多久,在内战爆发前己去到北平。
北平解放后,于浣非仍留在北平,並以其母名义登报寻找一九三七年去延安的小妹妹,未果后,方离开北平去香港。一九五零年前后,曾经在香港<东方画报>发表纪念肖红的文章。去台湾以后,以经营古玩谋生,研习中国画並致力于古籍整理。一九七八年在台中病逝。遗著有:<老子詳训诂>、,<庄子詳训诂>、<屈赋正义>、<诗经正义>等。
六、于浣非简评。
在日伪时期的地下革命活动中,与于浣非共过事的一位中共老党员,在遭受文革獄火磨练重生之后,于八十年代初,在北京开会时,从北京专程去天津看望于浣非的妻子。对住在女儿(于正之)家中年事己高的于浣非的妻子李相云这样讲:嫂子,应该劝于大哥回来。他过去对国家和人民是做了很多有益的事的。他对我们党也是做了很多有益的事的。
另一位也是高级干部的老党员,在历经文革浩劫之后,在北京对也曾历经生死磨难的于浣非的老弟(于甦)讲:建国后,我就在找你大哥,我感谢于大哥,在日伪时期,他在哈尔滨掩护我,给我治病,每天陪我在松花江边散步。
其实,于浣非只是中华民族众多爱国者中的一员。他毕生热爱自己的祖国,与人民融为一体。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
他以国事为重,抗战为先;他淡泊名利,清廉无私;他至诚待人,不求回报。是一位正直仁义的中国人。
他没有获取权力的欲望,没有物质占有的欲望,他从不为自己的妻儿子女牟取私利。
他甚至于没有担当起养家糊口抚育子女的责任,他不是一位好丈夫,也不是一位好父親。对他的父母,他没有履行孝道和赡养的责任,所以也不是一个好儿子。对于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他也没尽到扶助关爱的责任,所以也不是一位好兄长。但是,他热爱祖国,仗义朋友,弘扬民族正气。
他一生坚守他年青时公开表明的,要继承孙中山先生意志的诺言,生体力行地实践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誓言,于国于民,他堪称得起爱国者之誉。
他虽是早期的国民党员,但他没有政党派别成见,在抗日的全部活动中,他一直坚守着抗日爱国的信念。从哈尔滨到武汉再到成都,他一直与中共党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甘愿冒个人和家庭、親人生命的危险,去帮助、保护和营救共产党员。
他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北平解放后,他仍留在北平,期盼与共产党员的小妹妹取得联系,希望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打算留下的心迹明显,未果后才离开的。他首选去香港而不是去台湾。他从香港给他在成都的四妹妹(于淖沁)来过一封信,在淡到是否去台湾时说:未来那里将会是一片火海,绝不可能是久留之地。不愿去台的心迹也明白无遗。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于浣非的全部生命活动,就是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工作。他爱国胜于爱家,他对待朋友胜过自己的親人。
他反对战乱,祈望和平,他能尽力而为则为之,无能为力则避之。他最终还是离开已经解放的北平和中国大陆,抛弃家人,经香港(香港是英国统冶的地方)过渡后去了台湾。
他到台后避开政治中心的台北,选择有文化氛围的台中定居,远离政治,重登文化艺术的方舟,在研习中国画和整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渊源之中找到归宿。
他最终的抉择,能詮释他政治是幼稚还是成熟?能证明他看前途是清醒或是迷茫?这都于事无补。但他出走给親人和友人带来的遗患,这让他的朋友和家人深深为之痛惜。
二零零七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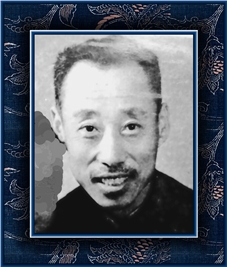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