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道路——韩倩之自传(6)
2、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51年6月底我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到了北京,也是我们第一次到北京,这个扬名中外的几个朝代的古都,回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一派生机盎然之气,第二天在大雨磅礴中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的生日,刘少奇作了报告。
我们一家住在华北局招待所,中央组织部在华北调了十几名地县级干部也陆续到了北京。在北京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后来又到天津逰览,还出海观光四十公里。
这时连之已怀孕数月,她不可能同行去西藏,临时决定她及孩子暂留北京,建中到育才小学读书,苏美、二儿子建青送幼儿园。
在北京遇到从西安来京公干的原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的两个干部,打听到杨文明的工作地址仍在延安,当即去信取得了联系,从那以后,我们不断给孩子买些衣物寄去。
七月底中央组织部让我带队去重庆西南局报到,离北京前华北局副书记刘澜涛为我们饯行。8月1日到达武汉,因等船票在武汉等候半个月,这半个月好像在蒸笼中度过的一样,昼夜汗流不止,电扇的风也是热的。8月15日登轮西行,在宜昌又换船过三峡,夜停昼行十二天才到达重庆,住西南局招待所,西南局组织部派人组织我们到北培,然后到北温泉过夜避暑,煞是凉爽。几天后组织部同志告诉我们,请示邓小平同志,邓说目前不往西藏派干部,政治还在人家手里,干部到那里也是窝在拉萨,派不上用场,决定让我们华北来的十个干部先进西康工作,等到条件成熟时再去西藏,华北来的十个干部暂留重庆,我们在重庆停留十来天,即去成都,住川西区党委招待所,又住三、四天即去雅安。雅安当时电灯不明,马路不平,过了国庆节,我们十个人即到了康定地区,西康省委让我们先去藏区工作,以便以后为进藏打基础。康定居民多数汉民,少数藏民。这儿有个水电站,因没啥工业,照明用不完,故机关每个办公室住室都使用电炉取暖。康定以北十五公里,还有温泉澡堂,只是海拔2600公尺,颇不适应,喉咙干,痰块总咳不完,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其他领导人均为清一色的山西人,临时分配我在地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协助部长刘长健工作,他们都把我们当成在那儿临时落脚,不怎么重视我们。
1951年11月在康定收到连之北京来信,她于9月11日又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建方,并与我寄来满月后的一张照片,她显得消瘦和忧郁,我一个人远走数千里,把她一个人及四个孩子撇在北京又没工作,她的心情能畅快吗?
康定地区地广人稀,多为藏区。地委决定在甘孜、玱塘建立两个工委,苗逢澍找我谈话,想让我到甘孜任工委书记,我答应考虑。我立即给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写了一信,反映华北来的十个干部窝在康定,有力量不能发挥,有才能不能施展,如一时进不了西藏,望考虑分配这些人的工作。不久中组部干部处副处长王敖来信说已告西康省委分配我们的工作,在我还没有表态去甘孜的当儿,省委已通知地委调我到雅安专署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离开康定前,苗逢澍拿我出一趟官差,我和一个统战人物,一个活佛相跟,驱车越雀儿山去道孚慰问军队,官兵多为藏族,途中曾到藏族牧民帐篷内与牧民寒暄,喝鲜马奶,曾在一个喇嘛寺住宿,与活佛喇嘛座谈党的宗教政策,解除他们存在的若干疑虑。在喇嘛寺外面石碑上还有当年红军在此驻扎时写的标语痕迹。
康定地委开会给我做鉴定,苗逢澍对我在康定半年的工作基本上肯定,尤其在我主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报告团的欢迎接待上搞得很出色,受到中央表扬,对雅安的冷落接待进行了批评,但康定藏族自治区副主席李春芳对我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提出批评,说缺乏组织观念,我不接受他的批评,刘长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
1952年初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没参加领导这个工作,但从参加会议上看到打出那么多大老虎、小老虎,在内心里暗自打了问号,这是否都是真的?
1952年4月中旬,我返回雅安,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告诉我到雅安专署任专员,数日后即上任到职。专署各科室负责人都是山西人,他们对我还比较尊重。一次我到省委书记廖志高家叙旧,他热情接待了我,问他莫延忠在何处,答曰出国当参赞了。到职不久即听到康定地委有人对省委让我当专员有意见。我这个外来干部是他们眼中的沙子,过去我眼目中从来没有认为党内还有这帮那派之分,近日稍有察觉,但觉得这是个别人认识问题,没当回事。1952年8月间,雅安地委副书记安庆珠调走,省委报西南局任我为雅安地委书记,原宣传部长何元夫任专员,西南局已批准下达,但康定地委闹翻了天,苗逢澍亲自出马,向廖志高强烈要求对我的任命不要公布,省委要重新考虑,并提出康定地委不止一人可做地委书记,因这是他山西帮派大发作,廖志高在他们压力下妥协让步了,并改任我农林厅副厅长,主管林业及森工。他们甚至说韩倩之有朝气,有干劲,就让他去搞森工,伐木头,国家建设急需木材,西康原始森林茂盛,他可有用武之地了。省委组织部长、农林工作部长、秘书长,都是山西人,廖志高处在他们包围之中,山西帮的主帅就是苗逢澍,他们胜利了。廖志高对我进行安慰,但也有苦说不出。这时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党内帮派的确在,而且整人,表面上还不失冠冕堂皇的虚伪宠儿。
1952年4月底,我派人把连之及三个孩子接来,她这时已被分配到华北妇联任行政处长,工作挺顺心,真不想来,我生气了,就让人接他们来雅安,她来后立即分配到地区妇联当妇联主任。这时我们两个人工作都很称心。五月间她去北京参加全国妇代会,回来时折到朝城,把三女儿苏东接出带到雅安,大儿子建中一个人留在北京育才小学念书,这时我的初中好友寇有信在国家计委工作,我委托他在星期天接到他家去,让孩子有些温暖气息。
1952年10月,我趁工作调动之机去成都治病,主要是双膝风湿性关节炎,不凑巧这时连之也去重庆开妇女干部会。雅安建方有个保姆照顾,苏美已上小学,建青送幼儿园,每个礼拜天送他就哭闹不休,苏东也送幼儿园,她不怎么闹(长时间与父母没在一起的原因)。有一天,我在成都口腔医院忽然接到雅安长途,说建青患了急性阑尾炎已住院,疼痛难忍,医生说需要动手术,但家长不在没有家长签字,不好开刀。我在电话上当即表态同意动手术,而且越快越好,千万不要拖了。动了手术发现腹腔有脓,经过紧急处理,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再晚两个小时,他命休矣!
医生检查说,我腿疼可能与扁桃体有关,在口腔医院摘了扁桃体,腿疼仍不见轻,又住华西医院拔牙,仍无效果,只好用电疗办法,一个多月好了些,此后三、四年内用各种办法治疗,如针灸、热敷、蜡疗、注射、封闭等仍除不了根,根本问题是雅安雨多、空气潮湿,风湿关节炎难以治好。这个病是1941年在延安发生的,以后到前方战争环境一天到晚行军,腿倒不怎么疼了。1951年进城后又疼起来,尤其到雅安后关节炎又发展了。
1952年底,我回到雅安即办手续去省农林厅报到,厅长陈少山也是山西人,口吃。适遇新三反运动,机关干部对陈少山的官僚主义作风意见很大,省委让我领导这个运动,廖志高有意搬掉陈少山,让我任厅长,但运动半途终止,由于山西帮的保护,陈少山仍稳坐钓鱼台,却不让我管农业、水利的事,只管林业及森工。我为了开阔森林工业落后局面,便带警卫员步行深入高山林区,在翻山时我腿疼,下山特别困难,都是警卫员搀扶着我才得下来,一个采伐区一个山沟视察,同伐木场干部及采伐工人谈心,交换意见,如何完成今年西康木材生产十万立方米任务,大家都感到问题严峻,困难太大,主要是高山上砍伐倒的园木运不出来。1953年木材生产任务主要在宝兴林区,这是1935年红军过大渡河长征到川西北必经之地,山高路险,有的地方在半山腰修了栈道才能通过。由于山坡陡峻,只能修筑木滑槽道,一根一根圆木往下放,因滑动速度大,常常园木出槽飞到山沟或山坡下面,不是摔烂就是再也弄不上来,即令把园木滑放到山脚下,离河道还有几公里,这几公里非修轻便铁道不可,不然运不到河边,经过请示西南森工管理局拨下一笔专款修了轻便铁道,到了河边要编木排,一个排好几个人沿河下放,因河水湍急弯陡,河内礁石很多,又来不及清理,三百里河道若要清理,工程浩大,一、二年也完不了工,木材成本就高的不划算了。1953年就在这种艰难条件下,从深山老林流放到雅安贮木场的不足五万立方米,其他几万立方米木材遇到山洪暴发沿雅河顺流而下,直到乐山进大渡河,有的流到宜宾进入金沙江,我们只好派人沿途在河边收集木材,有的即令捞上岸,木头也碰的少皮无毛、残缺不全了,还有的木材被沿河老百姓捞走了的,这年木材任务没有完成,而且在木排流放中有十来个工人丧了命,这下子可使得一部分老山(山西人)幸灾乐祸起来,一片责难声,并要追查我的责任,我自己也感到因人死财亡(国家受了损失),自己责任重大,我在省委会上作了检讨,要求处分,廖志高和公安厅长(也是山西人)替我说了话没给处分,并立即采取措施答应我的要求,为宝兴、天全两个伐木场调了两个县级干部做总支书记,又给森工局派了几个干部,1954年顺利完成十万立方米木材生产任务,人身安全也没出问题。
1954年省委任命我为西康森林工业局长,农林厅的事没有我的份了。当时全国森林工业局有几十个均为县级单位,所配局长最高十四级,把我这个十级干部放在专任森工局长位置上,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下子可称了苗逢澍之流的心意了,我倒了霉,他们就开心了。他们并不以打击排斥我而甘心,1953年底,薛连之的地区妇联主任被撤掉,说得漂亮为了使妇女参政树个典型把她派到雅安县任副县长,以后又改任雅安专署任监察处副处长。他们排斥异己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954年春天,杨文明从延安写信来,实行工资制后,他对孩子上学负担不起,要求我支援。这时我向他提出是否可以把苏荣(由苏亚改的)送到我这儿来,她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由我负担,孩子仍是两家的,他来信同意让我派人去接,我立即从森工局派一个干部到延安。几天后这个干部来信说杨文明夫妇提出要500元抚养费,为了把孩子接来,从机关借了300元,凑够500元寄去,很快大女儿来到我们身边,她已9岁了,又黑又瘦,满口陕北腔,但她眼睛明亮,精神烁烁,我又疼又喜又爱,高兴极了。连之为她买两套新衣服,五个孩子集合在一起,真是喜人,苏荣、苏美读小学,建青、苏东入幼儿园,建方留在身边。54年夏天,北京森林工业部召开森工局长会议,那时四川交通不便,第一次从重庆乘飞机去北京。会议期间看望寇有信一家,到育才小学看大儿子建中。会议结束时,正值小学放暑假,我带建中回山东老家看望父母。7月16日只身返雅安,路过西安,看常香玉演出,极有兴趣。7月19日乘机过秦岭,快到北培时遇见雷暴险些机毁人亡。
1955年肃反运动中开始我掌握较稳,无论如何在森工局不能发生逼供信错误,事情的发展我作不了主了,仍出现了逼供信现象,自愧无能,只有随大流了。
1953年7月9日我们的小女儿在雷雨中降生了,起名苏雷。
1955年8月28日我们的小儿子出世了,生下来一称八斤重,故起小名八斤(现名韩建欧)。
在雅安已有七个孩子在我们跟前,加上在北京的大儿子建中,正好是八大员。
1955年秋天收到老家电报母亲因患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她老人家做一辈子牛马,没有过一天幸福日子就走了,我不禁痛哭失声,与连之商量,急欲奔丧故里,无奈相距遥远,交通不便,她劝我勿过悲痛,于是把仅有的几百元钱寄回家托二弟负责安葬,母亲死时才67岁。
1955年11月中央决定撤销西康省建制,并入四川,恰逢此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建立,急需各省派干部支援西藏工作。快要结束的西康省委又点名我夫妇一起进藏,那时中央决定凡进藏干部不允许带孩子,因高原空气稀薄,不适儿童成长,我们跟前七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才三个月,怎么安排?但我夫妇没向组织上叫苦,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那时患高血压病,便让我到成都治疗,再加治关节炎,几个月仍不见效,四川省人民医院大夫说我低压120,不能进藏,他们要向省委反映,次日即见报我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农林处副处长,我说国务院已把任命公诸报端,没让人民医院向四川省委反映,就准备动身启行。
西康省委结束时,组织部给我做的鉴定,我看了真叫人生气,他们在西康整我还不过瘾,还要让西藏党组织认定我这个人不能重用,缺点一大堆,至于优点么,对不起,一点也没有,我在他们给我的鉴定表上提出了保留意见,他们要整我远没有到此为止,1956年工资改革时,西藏征求四川省委组织部意见我和薛连之调级意见,他们答复二人均不调级,这次调级几乎是普调,他们仍对我们来个落井下石,我真佩服这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肖小之徒,欲把别人至于死地而后快所采取的卑鄙伎俩,作俑的仍是苗逢澍及组织部副部长苗某,他们整人可自鸣得意于一时,但他们的卑劣嘴脸终于会被人识破的,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苗逢澍满以为以西康省委副书记身份合并到四川,再给个省委副书记还不是十拿九稳吗?对不起,他只获得民委副主任职务,一直到他离休,他也只在水利厅长职位上,再没前进一步,四川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对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反过来说,我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得罪过他们?想不出来,领教了,可爱的先生们!
我们把三个大些的孩子送到成都市育英小学,三个小些的孩子分别送进两个幼儿园,最小的儿子八斤请保姆带着,住在四川森林工业管理局,我们于1956年6月10日上路了,我们上汽车时孩子们都眼泪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眼含热泪分别了。
成都到拉萨的川藏公路2300多公里,全线通车还没有多久,从四川支援西藏的干部大队共40余人乘坐两辆旅行轿车,省委指定我为大队长,建立一个临时支部。翻过二郎山,穿新修的泸定桥到康定,然后到达甘孜休息两天,翻越海拔五千米的雪山到金沙江边的德格县城,过金沙江后到达郎达草原,然后到达澜沧江边的昌都,在昌都停留五天继续西行过怒江,真是名符其实,湍急的江水发出怒吼,西行至然巫,又走了两天即到小平原曲麦,这儿海拔较低,气候温和,休息三天,因为曲麦西边数十公里处,高山冰川倾泄,把公路冲毁,短时间难以修复,只好往拉萨发电报派车到冰川西边迎接我们,还好,冰川经过的沟口有个小铁索桥,可以通过行人,这样人和行李经铁索桥过到冰川西边,换乘迎接我们的两辆带帆布棚的卡车,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7月4日才到达拉萨。
西藏工委书记也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三,副书记范明都热情地欢迎接待了我们。前三位待人诚恳正直,唯范明有旧军阀旧官僚习气,因他长期做旧军队统战工作养成的坏习气,因他是专职副书记,他虽排在张国华后边,但他却主持工委日常工作,飞扬跋扈,我看不惯这个人的骄横、庸俗、拉拉扯扯的腐败作风。初到后他对我夫妇格外亲热好像旧友重逢,无微不至地关怀极尽拉拢之能事,连之和我都很反感,以后就有意避开他,几次邀请到他家做客,除第一次应酬外,就再不赴约了,二张一谭和我相处能谈得来。进藏不久,除让我任农林处又兼畜牧处长外又报请中央批准任命我为工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我实际工作在筹委会两个处,主要工作是统战工作。我与日喀则派来的农林处副处长相交甚厚,能赤诚相见,互相尊重,他常个别交谈时反映藏族上层人士的内部情况,在达赖喇嘛去印度朝圣期间,西藏地方政府一些官员抵触将要出台的民主改革,酝酿叛乱,不让达赖回藏,并图谋武装叛乱,藏军公开在大街上游行示威。那个副处长及时把所他了解的将发生暴乱的情报透露给我,我就随时报告了工委。西藏军区采取紧急防范措施,在军区院内检阅部队及轻重武器,又在拉萨东郊举行空降兵跳伞表演,都邀请了拉萨上层人士参观,以奏威慑之效。在这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五次找达赖面谈,晓以利害,并答应他中央同意六年不改革,1957年初达赖回来,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说来也怪,我到高原后血压却不高了,但又出现频繁地心律不齐,心跳过速,120/分,胸部产生失落感。1957年4月初连之率领西藏妇女参观团去内地了,张经武、范明也不在拉萨,又加上因不搞改革,农工部机构撤销,我以心脏病为由给张国华写信要求回内地,过了两天他找我谈话同意我回内地,我马上通知正在北京的薛连之,她可以不再回拉萨了。
在西藏高原整整呆了一年,体重减少15公斤。我于1957年7月12日乘苏联吉普车走青藏公路,用五天时间到达西宁,在西宁住了两天,即到兰州。这时中央组织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就在兰州分配从西藏回内地的干部,就地派遣到各地,原则上何地来藏的再回何地去。工作组同志问我是否还同意回四川?我以腿疼四川气候潮湿受不了,不愿再去四川了,实际上那些整我的人还在四川省委组织部,我就是没有腿疼病也决不愿再去受他们摆布了。经过电话协商,河南省委同意接收我夫妇到河南工作,我也知道河南穷困,各方面工作也比较落后,但平原省与河南省合并后,还有几个熟人如宋玉玺,所以就决定到河南,这下子就决定了我下半生的命运。
1957年8月初离开兰州到宝鸡,转乘新通车的宝成铁路去成都接我的七个孩子。从宝鸡到成都火车行走特慢,走了两天两夜才到达成都,到森管局落脚,局长韩正夫热烈欢迎我的归来,等他知道我已确定去河南时他凉了半截。首先在幼儿园看见八斤,他长得结实饱满,我很高兴,最使我心酸的是见到小女儿苏雷,她已四岁,见我时呆如木鸡,因她在一年内谁也没接她出去与姊妹们团聚过。两天内几个孩子都集合在一起,煞是热闹,还好,孩子们没害过什么大病,我在成都用了几天时间带着孩子们逛公园、影院,尽情玩耍了几天,我和孩子们都兴致极高。
我和警卫员、保姆带了七个孩子于1957年8月下旬到达郑州,当天晚上我即去宋玉玺家拜访他,他那时是省宣传部长,他又把组织部长张建民叫来共同商谈我的工作问题。我来郑州前他们已商量个意见让我到高等学校工作,我说我这个人很粗,很鲁莽,不适宜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是否换个别的工作,我愿做地方工作,农村工作。他们说,高等学校右派进攻很猖狂,我们党还没有占领这块阵地,目前中央正在从各条战线调得力干部去占领这个阵地,正好你赶上这个浪头,打退右派进攻,没点魄力是不行的,相信你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你会打开局面的,让我好好学习一下最近毛主席两篇文章即:《论夏季形势》、《事情正在起变化》,按照毛主席指示请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最后确定我到开封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让我先去工作,等候中央任命,如此这般到了开封。下面谈谈开封十六年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1957年8月28日我带领七个孩子到开封师院,院长赵纪彬正在为难以对付学校的紧张复杂局面而发愁,他是个学者,对政治斗争缺乏经验,这下可好,他把开学后反右派斗争的全部领导重担都卸到我的肩上了。在党员骨干会上他介绍了我党委书记的身份,但在全体师生大会上他把我介绍成党的负责人,这也难怪,因为宣布职务没有文件根据。
我到校后因人口多,没有合适的房子住,只在我的办公室支了六个床,男女同室,保姆带八斤住在一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内,我住在大办公室套间内,把孩子的小学、幼儿园安排停当,即筹划开学后继续开展反右派斗争的事宜。事实上反右派斗争已到扫尾阶段,在教师干部和个别学生中所划右派名单已报上级审批,只是整理材料,进行系统批判就是了。九月下旬省委召开全会扩大会,传达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讲话精神。毛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把1956年党的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给否定了,我当时在思想上毫无保留的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说明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要与当权的无产阶级较量,那就只有奉陪到底了,从此,我的左倾蛮干思想和行为就扎下根了。
1957年9月底,我在郑州开会期间,薛连之的西藏妇女参观团任务结束,她把藏族团员送到兰州,又返回郑州,我到车站去接她。半年没见,她在内地生活好,身体更结实,并显得年轻秀丽。一对恩爱夫妻的重逢从精神到肉体呈胶着、溶粘状态,如胶似漆、如糖似蜜,不亚于21年前的新婚燕尔,美满幸福极了。省委组织部分配她到省妇干校任校长,妇干校就在开封,会议结束后回到开封,她与孩子们见面,她与孩子们分离已一年多了,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把她围了一圈,她轮番亲吻了每个孩子的脸庞,我们全家在院内照了几张合影,师院的同志们看到我们幸福的家庭都很羡慕,在师院前七年,我们始终没住上成套宿舍,一家老少十几口人零零散散分居着,但由于我夫妇恩爱无间,全家充满欢乐愉快的气氛。在天灾人祸极端困难时期的1961年8月10日,孩子们还给我们举行银婚纪念活动,虽然由于营养不够全家人体重都减轻了,孩子们都面黄肌瘦,但精神都是愉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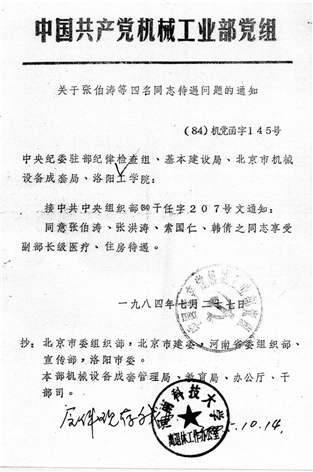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