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道路——韩倩之自传(7)
1957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来通知:中央批准任命我为开封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但这时学院还没有建立党委会,这个书记不是成了无本之木了吗!?尽管如此,在全院大会上还是宣布了中央的任命通知。我便以改造者自居,知识分子都属资产阶级范畴,都是被改造对象,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深信不疑。1958年3月,开封师院党代表会议召开了,选举了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我为党委书记。这时广大学生为向党代会献礼自觉开展了向党交心运动,把自己赤裸裸的一颗心呈现给党,有的把多年的日记全部交了出来,有的把自己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这说明广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并表示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做党的好儿子、好女儿。这足以说明大部学生是真心诚意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党代会一结束,党委就号召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向党交心运动,大部学生都卷进这个热潮中,但教师却表现得比较冷淡。因57年鸣放后划右派的教训,对他们来说如芒刺在背,所以他们对此举噤若寒蝉,不敢轻举妄动了,怕重蹈去年一些人的覆辙,这是不足为奇的。在交心运动的基础上,1958年4月我发现在少数青年教师和学生中有为个人主义唱赞歌,引起了群众性争论,我挑选了有代表性的、持不同观点的十来个人在小礼堂举行辩论会,争论的很激烈。我在讨论会结束时未曾表态谁是谁非,我倡议举行大会辩论,在大礼堂召开全院人员大会,讨论两个半天,两种不同观点展开面对面的辩论,会场气氛极为活跃。持集体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动力的观点占优势,持个人主义是推动力是极少数人,他们最后把观点修改为集体主义是大马达,个人主义是小马达,两者可以相辅相成,有的还坚持认为千千万万的个人主义的总和就是集体主义,我最后做了总结,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能相容,我们过去搞民主革命就是靠集体主义、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全心全意为人民,在刑场上视死如归,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推到了三座大山,这种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仍要发扬光大。个人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范畴,他对社会主义来说只能是腐蚀剂,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性,更谈不上有什么推动力,旧社会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有个共同信条,那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是社会主义新社会,决不允许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和膨胀,大家要团结起来,对个人主义群起而攻之,要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使它无藏身之地。这场大辩论后,对围歼个人主义的发言选了若干篇出了专辑,会后对持个人主义观点的并没有采取组织措施,没处分一个人,也没处理一个人,也没组织围攻一个人。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长期的,绝非开几个辩论会能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但这场辩论在全院师生中震动不小,它对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起了促进作用,据我所知,当时中文系一个学生作为持个人主义观点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后也没遭到歧视,更没有带帽子,打棍子,59年毕业后还留校,现在已提为正教授,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尽管如此,大会辩论我做的总结把个人主义比作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什么群起而攻之的说法很难使人心服,有凭势压服的味道,这是不足取的。如今看来,集体主义少了,又不那么兴时了,个人主义不但受不到抑制,反而泛滥膨胀成灾,由个人主义到极端利己主义到“一切向钱看”,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坑害国家、坑害人民,无所顾忌如“官倒”、“私倒”、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假药假酒盛行等等腐败现象,还不是从个人主义发展起来的吗?
紧接着又在全院范围内展开“红专”大辩论,教师和学生都参加了辩论,最活跃的还是学生,大家都能畅所欲言,从教研室、系到全院大会展开辩论,我认为这是群众教育的好形式,在辩论中有几种看法:以专为主,这是报效社会主义祖国的看家本领,没有坚实的专业基础是不可能把本职工作搞好的,指导思想是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政治上过得去;只求专不求红,专是根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红”也不能一点不要,有点粉红颜色就行了,“红”不能当饭吃;先红后专论,认为红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红”做统帅,再好的业务也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首先要“红”,然后才能考虑“专”的问题;又红又专论,认为只专不红会迷失方向,自己犯了大错误还不知道是怎么犯的,如果只红不专,很可能发展成为空头政治家,人民也是不欢迎的。最后我做总结,肯定又红又专的观点,有针对性的谈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强调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的重要性,要求知识分子要有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的决心。这两次群众性的大辩论收获不小,使更多的人打破了自己的糊涂观念,提高了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自觉性,但自我思想改造是个长期奋斗过程,绝非两次辩论就能解决问题,每个同志要有个红专规划,在思想改造上有两个途径必须遵循: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掌握这个改造世界观最犀利的武器,但这还不够,还必须知识分子劳动化,建立工农感情,这种感情光从书本上是得不到的,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到工人中间去,到农民中间去,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没有体力劳动的大量汗水,是达不到劳动化的境界的。因此我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经途径,在我这个思想指导下,在大跃进年代,我把广大师生(包括55岁以下的老年教师)都毫不例外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上山采矿,下乡与农民一起劳动。58年下半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劳动时间有2/3,上课时间不足1/3,过后青年学生和教师谈体会说:肩膀压肿了,思想练红了,业务呢?丧失了些。我在大会上讲,这是个大战役,有得必有失,得失相较是划得来的,所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是长远起作用的,损失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是可以补回来的。在下乡上山锻炼中,我是跟着大家一起同甘苦的,上山采矿下煤矿挖煤,在田野劳动我都参加了,各系党总支书记都随同大家一起拼命干,所以那时党的威信很高,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那个年代的在校学生现在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相当多是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他们见到我谈起来都说那是难忘的岁月,感情弥深。
在这期间,由于我脑子过热,把社会上的盲动也移到校园内来,大办钢铁全民动手,为使钢铁元帅升帐,学校怎能袖手旁观,先由坩埚炒钢,到小土炉,以后发展小洋炉,社会上放钢铁卫星,我们在院内也放一昼夜炼铁十七吨的卫星,我同大家一起二十四小时不离炉旁,为了解决原料不足,我常带头把家的铁锅及其他铁质炊具用具砸烂填在小土炉里,把学生宿舍取暖的煤火炉都砸烂填在炼铁炉里,铁是炼出来了,但杂质太多,名曰灰生铁,实际没啥用,这不是劳民伤财么?还有58年8月中旬我带地理系师生到商丘北郊,毛主席刚参观不久的一个公社,参加两周的农业劳动,那个公社名曰八八人民公社,是由于58年8月8日毛主席亲自去那里参观而命名的。我们看了该公社的小麦试验田名曰八八试验田,即每亩地深挖八尺,上八万斤肥料,播800斤麦种,产量八万斤。他们敢想敢干到这种地步,我不敢泼冷水,但我算了一笔账,亩产八万斤,铺在地上有多厚?大约半尺厚,这不是荒唐可笑么!我们从商丘回来,大家热气冲天,纷纷提议把院内一个小花园毁掉约六分地,我们来个六六试验田,翻地六尺深,上六万斤肥料,播600斤麦种,计划亩产六万斤,我对这股热劲也不敢泼冷水,说干就干,不到三天挖成了,肥料也送进去了,一个月后硬是把600斤麦子撒在这六分地里头,第二年收成还没有下的麦种多,这就是对盲动蛮干最结实的惩罚,也是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唯心主义的严厉惩罚,也是对吴芝圃《哲学的跃进,跃进的哲学》主观唯心论的尖锐讽刺,我自己也滑到了天真幼稚令人啼笑皆非的境地。
1958年我在学院又掀起了拔白旗运动的热潮,目标是针对有学术成就的老年教师,主力是学生,我到各系发动学生拔老师的白旗。我当时理解白旗的概念是治学方向问题,是重业务轻政治的问题,是学术上的厚古薄今问题,没有认为它是个政治概念,没有认为这是敌我矛盾的范畴,而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故我号召教师要主动自己拔自己的白旗,再在自己的脑子里插上红旗,我也曾个别动员院长赵纪彬带头拔自己的白旗,他不接受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白旗,而且态度坚决,我没有勉强,更没动员群众拔他的白旗。因为用群众运动方法拔白旗,后来局面就控制不住了,各系自作主张,白旗越拔越多,简直白旗如林,于是我召开各总支书记会议,采取急刹车的办法,勒令停止,河南省委文教部召开了各高校党委书记会议,还让我向大家介绍拔白旗的经验呢!我内心很空虚,深感白旗拔过了头,拔得太多了。这次拔白旗运动大大伤害了老年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1958年底陈毅副总理到学校视察,让我汇报学校公社化的情况,其实我的心思没在这上头,如家庭建立洗衣组、缝纫组等我过问的不多,营业收入具体数字我说不清楚。
1958年河南省全省开展反潘复生运动,主要批判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小农经济优越论”,把潘复生当成阶级敌人进行批斗,并要在各地区各单位挖小潘复生,开始,我在学院只让大家学习报纸上的反潘复生文章,没挖小潘复生,省委书记杨蔚屏到开封市开会讲话点了学院的名,说学校难道是世外桃源?难道学校就是阶级斗争的风浪吹不进的一片干净土?我沉不住气了,于是又在学院开展了反潘复生运动。因为在学生中不少农村来的学生对潘复生的观点表示同情支持,据此在学生中挖出小潘复生,名曰潘复生的应声虫。开始我没有考虑划右派问题,因受全省第二次划右派的影响,于是把应声虫也打成了右派,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记得是在1961年初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亲自到河南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纠正吴芝圃的错误,吴芝圃错误之一就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潘复生、第二次反右派斗争。陶铸决定这次划的右派一风吹,统统予以平反,这项举措是很英明的,学校迅速的给第二次划的所有右派进行平反,已毕业分配了的把通知送到所在单位,没有分配工作到劳动场所改造的,一律回到学校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这是又一次的瞎折腾,损伤了纯洁坦率的青年学生赤心向党的感情。
1959年初中央宣传部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个会议。陆定一领导主持这个会议,康生也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身份参加这个会议。在总结中陆定一对1958年教育革命进行总结,肯定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贯彻取得的成果,他主要指出教学秩序被打乱影响了教育质量,强调今后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真正做到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国家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康生讲话则强调学校大搞群众运动,在战天斗地中增长真本领,要开门办学,不能闭门读书,把学生培养成书呆子。我们回来后,主要贯彻陆定一的总结精神,恢复教学秩序,按国家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办事。59年上半年学校教学纳入正常,学习空气浓厚了,学校环境也比较平静了,教师和学生都比较满意。
这时我采纳了院长赵纪彬等人的意见,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主,不能动不动就停课搞劳动搞政治运动,不能认为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我们两个人平时经常有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我被他说服了,我在极左思想支配下脑子热得厉害,他不断向我泼冷水,慢慢使我清醒了。
好景不长,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斗争及以后在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使我的脑子又热起来,我认为赵纪彬、曲乃生等人右倾,在学校反右倾运动中批判了赵纪彬、两个副院长曲乃生和杨纪高、宣传部长杜百根,把杜百根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杨纪高打成严重右倾,我和一些同志的极左思想又炽烈泛滥起来。60年又大办钢铁,教育厅拨给60万元修小洋炉,学校校园的学习环境又被打破了。秋天我把一千多名师生(包括老教师)带到开封县去深翻土地日夜干,这时全国缺粮严重,公社大锅饭还在吃,但没有粮食,以红薯叶、豆糁儿代替,学生劳动重,又吃不饱,不少人生病,身上浮肿。我用两天时间到各村走走,自己亲身尝到生活苦的滋味,感到如不及早收兵回城,要出大问题,于是及时做出决定把队伍撤回来,医生检查,一半以上的人患浮肿病,这时学校的伙食下降,口粮标准降到26斤,又没有副食,我带头到城外摘树叶渡荒。这时社会上灾荒严重,信阳、商丘地区饿死人消息传来,学校真可怕!学校虽没饿死人但一半以上人得浮肿病、慢性肝炎,这是极左路线造成的结果,是客观规律给我们的严厉惩罚。我一家十来口人吃不饱,我把在西藏积存的几千元钱用高价买红薯、南瓜填孩子们的肚皮。
1961年高教60条下达,学校教学秩序又纳入正轨,但一时也恢复不了元气。62年我在全院大会上宣布给所有拔的白旗平反,摘掉白旗帽子,并宣布给所有教师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并宣布都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这是开封师院有名的脱帽加冕大会。此后我逐门逐户拜访受伤害的老年教师向他们赔礼道歉,并亲自去北京向院长赵纪彬赔礼道歉,向家居北京的老教授常玉璋赔礼道歉,竭诚欢迎他回校工作,他本来不想回学校了,因我衷心承认错误,诚意请求他回校,他受了感动答应回学校,以后几年我常去他住处造访谈心,我们成为好朋友。还有如名教授孙作方、华中彦等,我们都化干戈为玉帛了,我是他们家的常客,感情反而更亲近了。教师们对我有这样的评价:韩倩之“左”起来左得天真,左得出奇,左得无情,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又能披肝沥胆,真心诚意面对面承认错误,老干部做到这一条也是难能可贵的,故原来感情上的裂痕很快就弥合了。
追述一件不愉快的事,这件事刺激了薛连之,造成了她精神上的痛苦和扭曲。1958年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历史系一个女学生拼命追求我,写信为我要献出一切直至生命,我没理她,但在58年春天我住院医治肛裂时,她两次到医院看我,她毫不掩饰的吐露她仰慕我直至下决心要得到我的心情发展过程,我婉言谢绝她的恋情,一再向她解释我是有八个孩子的父亲,我和薛连之是恩爱夫妻,我这个家庭很幸福,请她无论如何不要插进来,对我对她都不好。我出院后她仍在信上执着的表示她不能没有我,并且寄她一张照片给我,正好被薛连之发现了这个照片和信,她伤心透了,精神刺激特大,我向她解释,我和那个女学生没有发生过任何越轨行为,我当着她的面把照片撕掉,立即写信让那个女学生再也不要写信给我,我决不再见到她。此后我再也没有同那个女学生有任何来往了,虽然我遇到过她,从她的眼神里透露出莫大的悔恨,但我再也没有理睬过她。但这场感情上的风波却很难使薛连之平静下来,每当她发现我同青年女学生接触谈话时,她敏感受不了,她怀疑至肯定我同从四川带来的保姆有不正当关系,她跟随我们六年,苏雷和八斤都是她带大的,没有办法,只好打发她回四川老家了。以后她的疑心病更加发展了,凡家里来了人,不管老年、中年、青年她都怀疑同我有不正当关系,怎么解释也打消不了她的疑心,我又同情又可怜她。
有个隐私,我从来没向任何人流露过,也写在这儿让孩子们及后人评说吧。
1959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分到开封师院一名女毕业生,中文系是我蹲点的系,在她所属的教研室参加活动,我为他的美貌而震惊,中文系党组织告诉我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业务水平不高。每逢大礼堂开大会,她总坐在前几排,当我看到她时,她的两颗水灵灵的眼睛总是望着我,这样四只眼睛对望时间越来越频繁,眼睛是灵魂的窗口,眼睛会说话,在半年之内上十次开大会,两个人的视线一接触就牢牢拴在一起了,我怕别人发觉,有意横扫礼堂数千人听报告者的表情,有时有意躲开她的视线,但当我再看见她时她仍在执着地望着我,我的心旌摇动了。冬季每星期六晚上交际处邀请学院开大车送女生去那儿跳舞,有次我见到她问会跳舞吗?答曰会,今晚去吗?反问你去吗?我说去,她说我也去,就这样由大礼堂眼睛说话到舞场上随着音乐及舞步的旋律,两个人均陶醉在无言的心心相印,飘飘欲仙的境界中去了,她几乎成了我唯一的舞伴,每当别的女学生邀我跳舞时,我不好拒绝,跳完一曲后走到她身边,问她为什么不跳,她很委屈似得羞怯怯的小声说,不愿同别人跳,并显得很孤独的样子,一次没同她跳,她就不高兴,她对我全面的占有欲是那么强烈。在跳舞中她的含情的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我的灵魂颤抖了,我比她大二十二岁,她是那样无保留的倾心于我,她长得又那么漂亮,身材窈窕,皮肤白嫩,性情温柔,说起话来莺声燕语,真使人神魂飘荡。60年秋她参加开封县深翻土地回校后见到我悄悄的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下决心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次在劳动中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她却吃胖了,白嫩面皮变得又美又红,她说她拼命劳动再孬的饭也能吃进去,也能消化得了,她微笑着问我,你看我能行吗?意思是说你满意吗?我真想把她抱在怀中用长吻吐露我对她的深深的爱恋之情,我相信,她久已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我克制自己感情的奔放,我若不谨慎一旦陷入爱的涡流拔不出来,后果是严重的。我若同这个24岁的姑娘结合,八个幼小的孩子置于何地?把薛连之不是要置于死地么?忘恩负义、喜新厌旧、新陈世美的罪名能逃脱得了么?堂堂数千人大学的党委书记能站得住脚么?我内心燃烧着炽烈的火焰被我的理智克制压下去了。这年冬,薛连之再也不允许我去跳舞了,春节除夕我没经她的允许去跳舞,结果春节也没过成,全家都不愉快。此后我再也不去跳舞了,我也很少见到她了,偶然见到,还是脉脉含情。我们两人之间谁也没说出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她没有勇气投入我的怀抱,我也没有主动拥抱过她,只能忍痛把茁壮生长的爱苗埋葬在内心深处。她一直等了我五年,直到1964年28岁时才结婚,1965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来往过。她现在已是53岁的老太婆了,她近况如何,是否还在河大工作,我没打听过,也不愿去打听了,我中年时期一段风流往事,就这样悄悄来临悄悄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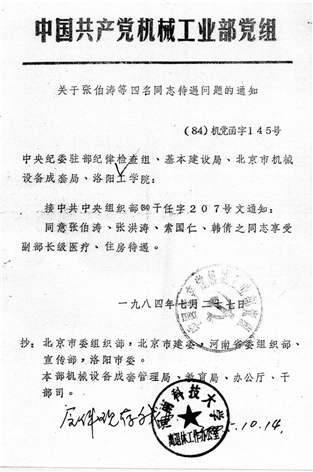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