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道路——韩倩之自传(4)
连之有了职业,心情畅快多了。我告诉她,战争打起来了,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准备过艰难困苦的日子。我还告诉她这次去开封完成学业的可能渺茫了,根据形势的发展我很可能奔赴抗日前线,她说:你走吧,你走到哪儿我也跟到哪儿。我把她搂在怀里亲啊,亲不够。
1937年8月底,我拿着连之给我的几十块大洋回到学校。这时平津流亡学生纷纷到了开封,我又把民先队组织起来,办了个壁报《钟声》,通过纪念“九一八”街头宣传活动,民先队与复兴社依照国共合作精神举行了谈判,决定两派不再互相攻击,团结合作开展救亡活动,民先由我和石正祥代表,复兴社李经伦和王子廉代表,大敌当前,既往不咎。这时学校功课又加重了,增加3月考,我感到这书是读不下去了,决定离开学校到山西去。暗中约集丁景仑、张开元、罗祖德、张文锐、路继训、王鸿洋共七人离开学校去太原,投奔穆欣(我们有通讯联系)。在太原国民师范停留一个星期,每天敌机轰炸,决死队成立,我们七人随决死队南下到赵城。由杜克介绍我入党,他说在行军路上我们讨论问题时我的认识水平比他还高,主要是指他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农民阶级的党,红军成分都是农民,我批判他的错误看法,我认为中共是工人阶级政党,看问题不能只从红军成分做判断,工人成分虽少,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世界各国共产党性质是一样的,后来他认识到他的看法不对。当时在决死队入党没履行手续,入党后决死二纵队即把我和丁景仑调到政治部工作,没几天八路军学兵队招生,罗祖德我们七人又一起去报了名。11月初到临汾兵站,太原失陷后北方局撤回临汾,11月13日北方局把在临汾的学员招集起来到刘村学习,在学兵队于12月又履行正式入党手续,我和丁景仑同时入党。次日即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政治处工作,都当宣传干事。我有了工作岗位,即写信给薛连之让她很快到山西来,38年2月初她一行六人到了山西,那时学兵队要结束,政治处把他们六人介绍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我二月初外出检查工作回来到民大见到她们。不久临汾吃紧,当时八路军办事处撤销,彭雪枫等去河南,因我爱人在民大,把我分到八路军总兵站工作,没几天兵站拟撤出临汾,派钟化银和我到吉县号房子,因走时突然,没来得及找连之告别,就拜托组织部干事赵淘在兵站撤退时把薛连之找来同行。二月底过了黄河问赵淘,他没办成这件事,我非常生气。后来知道民大也过黄河到了陕北宜川,当时总兵站驻在陕北延川,我贸然写信去宜川打听,收到了回信。我于38年5月初请假从延川到宜川四天路程两天赶到,见到连之,才知道她过黄河时遇见敌机轰炸什么东西都丢光了,一贫如洗。我在宜川停留两天,两个人一起去延安,三天路程五天才到,到延安后即持总兵站介绍信找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方强接见我们,次日我把她送到抗大四期四大队后又返回延川工作岗位。
我在延川总兵站,每月津贴2元,我把钱节省下来,三个月寄五元钱给连之。十一月她抗大毕业,毕业生大都分配到前方,因我在陕北工作,她被留下分配到军人合作社,当时主任是邱会作。1939年二月初总兵站搬到延安,这样我们每个礼拜可见一次面。
在延安半年,39年7月初我被分配到延水关兵站第二派出所当政治指导员,这时连之已怀孕,她不想让我离开他,我耐心做解释工作,走时托兵站政治处技术书记关子展照顾连之。当她肚子大时把她接到总兵站住,自己住在一个窑洞里。一天红小鬼给她室内生了一盆木炭火就闭门出去了,她躺在炕上睡觉了,那天下午她抗大同学陈介平(八年前是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任)去看她,敲门不应,推开门,满窑的烟气,看她在床上躺着怎么喊也叫不醒,知道中了煤气毒,很快把人叫来抬到洞外抢救,半个小时后才有气息。如陈介平晚去一小时连之就没有救了。当时我在延水关,延川分站派人去通知我说我爱人病重,让我立即去延安看望。听此消息如轰雷贯顶,立即动身到了延川,才知道是中了煤气毒,经过抢救已经脱险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分站长还是让我去延安看看,两天赶到延安同她相处几天,又陪她去中央医院检查说一切正常。这正是1940年1月底,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我只得又返回工作岗位。40年2月下旬正赶上兵站第二派出所要迁移到宋家川驻防,这时所长已去延安学习了,让我兼所长,本想在她生孩子时去延安照顾,但离不开,不好启齿请假。40年3月初机关到了绥德时,收到她的信说是二月底生了孩子但孩子出世后即口吐鲜血,四天即亡,这显然是受煤气中毒的缘故。这是我们第一个儿子只活四天就死了,她说她身体还好,还在兵站休息。40年兵站第二派出所又从宋家川搬到螅蜊峪接受任务,6月间连之从延安到了螅蜊峪,我们相处两个月,这是我们结婚后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段时间。这个驻地在黄河边,对岸是山西省的碛口,有次敌人隔河炮击螅蜊峪,我和她同机关人员一起躲在山沟里一天。不久总兵站政治处主任石忠汉率领一批党政人员到螅蜊峪检查工作,结果很满意,近一年来我任指导员又兼文化教员的工作,后来又兼管行政工作,各项工作任务都圆满完成,全所干部和战士共数十人,文化政治水平均有提高,精神面貌也好,主要表现在团结奋进,从延水关到宋家川到螅蜊峪,我平时都与干部战士生活在一起,除了给大家上政治课、文化课,教唱革命歌曲外,还与每个工作人员个别谈心,关心他们的思想问题、家庭问题。他们中的多数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陕北红军战士及从东北军俘虏过来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结婚,有个老红军已近四十岁也没结婚。这些同志不怕吃苦,不怕困难,革命坚决,心情愉快。只有一个湖南籍的红军战士爱说怪话,吊儿郎当,我个别帮助,班会上大家批评教育,他时好时坏,我忍耐不住了,骂了他,最后把他调走了。我有时对勤务员葛双基也发脾气,对一个四川籍的红军老战士关过禁闭,这是我工作中的缺点,巡视团对我提出批评,我接受批评,表示愿意改正。因我工作有成绩便产生了骄傲情绪,自认理所当然地行政、政治职务集中一身胜任有余,领导应让我继续一人独掌权。忽然听说去延安学习的所长梅振武学习结束回任原职,我个人主义发作,当即給总兵站部长张令彬,政治部主任石忠汉写了一封信质问我有哪些错误,兼职期间是否有失职行为,望给我指出,不然,当梅振武回来,我就要卷铺盖去延安听候发落。张、石联名来信严肃批评了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我感到惭愧了。自己有抱负想为革命多干些事,不能采取这种闹情绪以至要撂挑子的手法。这说明我在党内锻炼不够,自身的素质不高。拿刘少奇《共产党员的修养》(刚发表)对照自己,感到自己渺小的可怜。在一个小小的单位取得些成绩,就把它作为向组织讨价要价的资本,是可耻行为。这件事在1940年由石忠汉领导的在绥德召开的兵站干部会议上,我做了检讨。自那以后,自我要求比较严格了,更加注意自己思想意识的修养。
1938年春到达陕北后原来看不到的理论书籍一批一批地涌到面前:《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左派的幼稚病》、《战略与策略》、《马克思论中国》、《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论反对派》还有《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我手不释卷地一本接一本如渴嗜饮地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我把读书当成第一位的第一需要,反而对工作认为是琐碎小事,瞧不起。后来在党的生活会上,受到批评。开始还不乐意接受,认为真理都在经典著作的书本里,不很好读书怎么提高认识,增长本领。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反对教条主义,才真正从思想上解决了一些问题。40年看到巴比茜著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对斯大林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40年对《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由粗读到精读并逐段做笔记,我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真是根深蒂固,脑子里从来没打过什么问号,从来没有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十三年后斯大林逝世,我痛哭流涕,认为人类最高智慧的巨星陨落了,是全人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惨痛损失。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我迷信革命领袖,迷信革命权威达到盲目程度,长期以来我在工作中缺乏创造性,缺乏创新精神,恐怕根子就在这里。
1940年8月上旬我趁去绥德开会之机,让连之跟随我去绥德。会议结束以后她乘兵站汽车去延安,我返螅蜊峪。不久依照总兵站决定,兵站第二派出所移防到米脂县城。没有几天,所长梅振武返任,我被调去延安另行分配工作。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军委供给部与兵站部合并,名称为供给部,张令彬调任为供给部长,石忠汉仍为政治主任,我被任命为宣传科副科长,三个月后任宣传科长,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
在我任副科长伊始,张、石首长让我去兵站线检查工作,当时宣传科还没调来宣传干事,只我一人前去。从延安到绥德是随运光板皮大衣的大车队去的,到绥德后,由绥德兵站派通讯员送我到薛县,过黄河到兵站第二办事处,然后又到临县各兵站巡视工作,将近一个月才返回延安。1941年元旦后我又害了一场大病,是由于出差到晋西北途中由虱子传染了病菌,到延安后发作为斑疹伤寒,发高烧、说胡话,把连之吓坏了,送白求恩和平医院没有床位,不收,幸亏连之的抗大同学董纪南的爱人夏朝安是该院供给股长,托他的人情在病房内加块门板住进了医院。那时医院技术上诊断明确了,但没有治此病的药物,高烧发到摄氏41°,医生为避免合并肺炎就用冷水湿毛巾敷在胸部几分钟换一次,连之寸步不离床侧,她又把做衣服的布料卖掉用高价买几个梨削了皮喂我,吃点凉梨觉得很舒服,晚上连之不可能在病房陪护,则由值班护士喂梨换湿毛巾。由于我平时体质较好,终于把病魔抗住了,高烧慢慢消退了,从入院到能起床,连之始终如一地守着我,没有她的殷勤耐心的护理,在当时困难情况下我是战不胜病魔的。她是我的名符其实的命根子,对我来说,她恩深似海,一辈子我也报答不完。
1941年连之到新市场交通商店当总会计,夏天她有了身孕,这次我要尽力照顾她,使孩子能顺利降生而且要养活好,事先我俩商量好如果是男起名建中,是女起名苏亚。1942年1月8日孩子出世了,是个男孩,瘦小得很,只有五磅重,因为没经验,她奶头没突出来,孩子吃奶用力把她两个奶头咬破了,每次吃奶她疼痛难忍,眼里噙着泪花,这样,孩子换包、洗尿片、给她做饭都是我的事,在一个月内,我几乎把全部时间放到照顾她及孩子身上了,工作必然受到影响,政治主任及科内同志对我有了意见,党的生活会上对我进行批评,我不好作解释,承认自己工作没做好,再加上41年夏天机关外边的沟口上出现了《轻骑队》壁报,是讽刺小品文性质,我科宣传干事沈直东模仿轻骑队小品文口吻在供给部院内贴出讽刺机关科长以上小锅饭的特殊景象,受到部长张令彬在全体干部大会上的批评,并指出《轻骑队》之风不能仿效,要刹住这股歪风。我当时是机关党支部书记又是宣传科长,也不点名的批评了我原则性差。种种原因,我被下放到延安交通纺织厂当政治协理员,石忠汉原有意提我做政治副主任,由上述原因他改调兵站第二办事处政委,熊士存为政治副主任。
我于1942年2月带着老婆孩子到交通纺织厂上班,连之的任务就是带孩子。那时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都处在极为困难时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八路军每月60万元军饷停发了,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延安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那时机关双职工极少,有小孩的更少,公家每个人发给实物(如小米、布等)数量有限,不可能雇保姆,这样连之就不能工作,她也很苦恼,所以每逢八路军大礼堂发票观看演出,我俩便抱着几个月的孩子去看戏,来回走路就有25华里。我们的儿子随父亲的名字起名小布,因我那时改名为布刚,连之改名为薛良,后来到上小学年龄才改名为韩建中。小布才半岁,连之又怀孕了,她坚决不愿再生,不然就永远当家属,她不干,但那时若要实行人工流产必须主管部门首长签署意见,再到中央妇委由中央妇委书记批准才能去医院做流产手术。我去纺织厂没有多久(约半年)军委把交通纺织厂移交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由财政厅主管,为堕胎我找到厅长南汉宸签署意见,又跑到杨家岭找中央妇委书记李富春,李没在由他的秘书夏耘接见并代笔签署上李富春的名字同意人工流产。如此她才入中央医院由著名外科医生金茂岳做了手术,还很顺利,那时为怀胎四个月的妇女做人工流产手术不容易。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兴起,军委后勤部成立整风学习核心小组,部长叶季壮当组长,后勤系统科长以上干部参加,工厂由厂长裴味农和我参加这个核心小组,每周讨论一次,开始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参加小组几次会议,后来由总政治部主任王家祥派他的秘书陶铸参加这个小组,直到整风结束。通过整风学习,提高了对中央路线、政策的认识水平,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尤其在七大以后,毛泽东的形象更高大了。
1943年初边区政府决定交通纺织厂与延安难民纺织厂合并,我被介绍到民政厅分配工作,这时小布刚满周岁,已经学会走路,又白又胖,煞是可爱,但连之决意要去工作,不愿带孩子当家属,没有办法,只好把小布寄养在山沟里老百姓家中,公家发的东西全部交给人家,每个星期天我和连之去看望孩子,那家脏得很,有次去看见孩子在炕上睡觉,满脸都是苍蝇,嘴上、鼻孔、眼睛都布满着有几十个蝇子,心疼的直流泪,在群众家只待两个月,孩子面黄肌瘦也不会走路了。这时连之已在一个商店当会计,她无心把孩子领回去,我在工作分配期间,先在民政厅抚恤委员会帮忙,我想若再拖下去,非把孩子小命送掉不可。怎么办?我们商量结果送孩子去中央医院检查,我在抚恤委员会借一头骡子,小布的养母抱着他骑上,我牵着骡子走在大路上,迎面来个骑自行车的,骡子惊了,我也牵不住,一老一小摔了下来,孩子受惊没受伤,养母额上摔了大疙瘩,没办法我只得把孩子送到连之那里,又牵着骡子送保姆住医院,好在没伤着脑子,十来天她出院回家了,她不再管这孩子的事了。为了给孩子治病,连之只得请假带孩子去医院住在那儿,经过检查,小布的病是阿米巴痢疾,当时医院没有特效药,好在不久由大后方来的一位小儿科侯大夫自己带些药,给孩子服用,住了三个多月医院才把病治好,但一岁半了仍不会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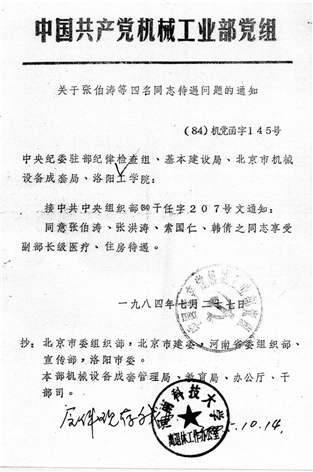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