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晖曲——作者:祝仲铨
春 晖 曲
中文系62级 祝仲铨
五十年前入校学习的时候,母校的名字叫“开封师范学院”,响亮的“河南大学”,是她曾经的辉煌和以后的“光复”。那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年。全国所有高校的专业和招生规模都大大地压缩了,不少院校被撤销或将主要专业并入其它院校。
在高等教育的惨烈与不幸之中,我还算是一个幸运儿。
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的幸运,在于我踏入了开封师范学院的门槛。
开封师范学院就是赋予我百折不挠、拼搏向上的精神、教给我做人、做事、做事业的本领的伟大的母亲。她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终生享用不尽的恩惠。
刻骨铭心的“训话”
一入学,便是院长助理、系主任钱天起教授的“训话”。
钱主任认为,中文系62级是本校十几年来录取分数最高的一届,比以往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还要高。踌躇满志的钱主任表示说,他对这一届学生充满信心。他设想从这一届开始,在教学上,要求教授给我们授课;在教研上,要求所有讲师在指定的教授指导下,完成既定的业务进修计划,提高教学水平。钱主任说,有科研任务的老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优质完成科研项目,并在系里公之于众。钱主任兴奋地对我们讲,从这一届开始,他要实现提升中文系整体水平、振兴中文系的愿望。他告诫我们,大学的学习,完全不同于中学阶段。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多,自学的时间充足。他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希望大家珍惜四年的学习时间,勤学好问,刻苦、努力,不要虚度光阴。钱主任说,我们虽然是师范院校,但从这一届起,还是决定参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安排教学,还决定,在这一届毕业时,要通过毕业论文、进行毕业答辩。
钱先生说,国家的经济正在好转,但目前还很困难。尽管如此,还是抽出一定资金,每月供给每位同学十二元五角的伙食费和一定的医疗费。学校会努力把食堂、校医院办好,尽可能地保障同学们的健康。但是也希望大家积极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保证以一个健康的体魄完成学业。
几十年后,一次和钱天起主任的公子钱大梁聊天,说到钱主任的“入学训话”不仅让我,也让我那一届同学刻骨铭心,享用一生。大梁先生感慨地说,老爷子(指其父钱天起教授)一生说话、做事谨慎,对你们还有这么一段讲话!他对你们这一届太偏爱了。
是的。钱主任的偏爱溢于话间。那天,他是在62级全体新生面前,在全系教职工面前,以系主任 的身份,严肃地、诚恳地、认认真真地讲的。
“训话”没有讲稿,现场谁也没做记录。但几十年来,每当我和同届同学说起“入学训话”,大家差不多都能把“要点”说得比较详尽――无论是后来做了厅、处级领导干部的、当了教授、研究员的,还是成为基层业务骨干、拔尖人才的。
因为,那“训话”体现了一个领导、一位长者、一位导师、一位学者对莘莘学子殷殷的期望、深深的眷顾与满腔的热忱。
现在看来,那“训话”似乎并没有大师级的高屋建瓴的那种警世名言。但是,那是讲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角奏响之时,讲在强调“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年代里。钱主任没有直接地、正面地教导新生们“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却能一直激励着一百二十几个学子在人生道路上奋勇直前,使半数以上的人成为领导干部、学界精英,其他也多为基层或某些方面的的砥柱!
五十年来,当学生时,我曾在职工夜校给学校的职工讲语文课;后来在农村参加“四清”,之后又到洛宁山区学校搞教育实习、当代课教师;参加工作后,被上级组织调动多次。当过记者、做过文化局、文联的干部,还当过期刊编辑;退休前十几年,又做高校的党务工作,其间又有不少的社会兼职。尽管随着岗位的不断调整,工作对象不断地变化,但是,对待工作对象的基本态度,那种“殷殷”、“深深”、“惓惓”,都是钱天起教授的一番“训话”的传授;不论在何岗位做何种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好,做出成绩的基本态度,也都是钱天起主任“训话”精神的继承。
所以,“文革”初始,当听说受到冲击的钱天起主任去世时,我躲在东工字楼与西工字楼之间的小道上,朝着钱主任家所在的南边的平房院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富有生命力的近代建筑
学校正门、大礼堂、六号楼、七号楼、东、西斋房······这一组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近代建筑,是曾经亲近过她们的河大学子的骄傲。五十年来,采访、调研、会议、旅游,走南闯北的参观,以及报刊影视媒体的推介,展示在眼前的所有林林总总、气象万千的各色建筑,都曾令我艳羡、惊叹过。但是,我总是禁不住与母校的这组卓绝的建筑群相比照。比照的结果,便是“叠印”;“叠印”之后,这组建筑群更加铁打钢铸般嵌在心底,而其余建筑的印象,则随着流逝的岁月,从脑海里淡出了。
每次去学校,我总是喜欢多走上几步路,从庄严肃穆的学校正门进去。跨进校门的那一刻,“我是河大人,我要刻苦、勤奋地学习,继承、弘扬河大精神”的人生态度与责任感,油然而生,仿佛有师长在身前身后耳提面命地训教一般。
河大图书馆的馆藏,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在全国图书馆中是出了名的。她还以所藏古籍书刊的珍贵价值和库藏量被国务院命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六号楼是我就读时的图书馆。我总觉得,她和七号楼就是母亲那对奶汁无尽的乳房,供我们充分地吮吸。我曾从六号楼借出许多喜爱的书。除了老师开列的参阅书外,还尽可能借来课堂上老师提到的书刊;除了学习参考书,还凭着爱好,去借感兴趣的书。比如,《二胡曲集》、《高松竹谱》、《芥子园画传》、《宋人画册》及浙、皖篆刻家作品选与著名碑帖。
一个细节令我至今难忘。有一天,我从六号楼借了书回十号楼教室,我边走边翻看着,途经七号楼时,索性就坐在其东门的石头台阶上看了起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到二楼的学生参考室(阅览室)里去看书。经这位老师指引,我找到了此后几乎天天来“泡”的学生阅览室。在这个理想的场所,我发现儿童文学作家余辰正在500格大稿纸上写着小说,高我两年级的学长拿着笔记本往稿纸上誊着诗作,外系的一个同学正从一本精装的外文书上摘抄着什么······这真是个“世外桃源”!在这里,我可以“不务正业”地抄记《良宵》、《二泉映月》、《江河水》以及《春江花月夜.》等带有弓法、指法的二胡名曲谱子,可以从从容容地用拷贝纸双勾《兰谱》、《竹谱》和篆刻佳作。当我把这个欣喜的发现告诉写诗入迷的杨子江、王怀让同学时,两人相视一笑。我这才知道,他们早就在那儿“悄悄地干活”了。
那天晚饭后,我早早来到学生阅览室,那儿已经是座无虚席了――一两个空椅子上,放着占座位的流行标志:坐垫。余辰拿开他附近的一个占位坐垫,说。先坐下来干活,人家来了,让给人家。但是,那天晚上,占座位的同学竟然没去,让我稳稳地在那儿读了两三个小时的书。那正是槐花儿飘香的季节,四周充盈着洋槐花儿所独有的甜丝丝、香喷喷的芬芳,沁人心脾。我走下七号楼,看月光从树间泻下,照着石阶下的小道。仰首望去,只见几颗粗壮的老槐树花开正盛,一团团,一簇簇白色的花儿随风摇曳,恣意地将芳香向四下里撒播着。我不禁张大口,贪婪地呼吸着,尽情享受天赐的这一切····
七号楼北边的大礼堂象泰山一样,安然地坐在学校心脏的位置。在那里,我们听时事与政治的报告,听杨尚奎等学者的学术演讲,看中央乐团、湖北歌舞剧院的演出和学校文工团的文艺节目,参观师生书法绘画作品展览····在那里,我们得以净化灵魂、启迪心智、开阔视野、提升素质····我爱这个地方。但是,我还独独钟爱大礼堂里那宽阔的壁镜。那是在河南大学工作过的著名教授对母校的一种纪念。他们的名字就镌刻在壁镜下端镶嵌于镜框里的铜板上:张长弓、范文澜、冯友兰、姚雪垠、顾毓秀、潘梓年····【务请编辑同志据校史校勘以上名单――笔者】每次到大礼堂,我都会来这里瞻仰一遍。每次瞻仰,都会使全身补足了精、气、神。这些著名教授虽然未曾授业于我,但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从他们名字里折射出来的成就学问、成就事业的力量。几十年来,每次忆起这壁镜,这壁镜上先师们的名字,都会为我人生的旅途加足一次燃料、使我调整一次步伐,更加顽强、不倦地前行。
说到东斋房,就得说说我们系的青年讲师。他们之中,被我们年级同学追捧的前几位是何望贤、周鸿俊、何权衡等先生。他们和其他讲师就住在东三斋、东四斋的阁楼里。我有几次是被老师叫去接受“耳提面命”的“辅导”,也有几次是“立雪程门”,主动的讨教。小阁楼里的格局挺有意思。一套房子住两位老师。中间部分背靠背放着的各自的书架和共用物品,讲房间分为东、西两个居室。每个居室有一堆满了书报杂志的小书桌。印象最深的是小书桌上的灯,虽说不足以耀眼,但远比我们宿舍的照明要亮的多。
何望贤老师给我们讲文艺理论。他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片段时,既不看卡片,也不看教案,而是用他特有的湖南腔,滔滔不绝地给我们援引着,津津有味地赏析着,讲到动情处,甚至还会飞溅出一些唾星。周鸿俊老师则是慢条斯理,缓缓而言。他的讲课时常要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其他作家的作品。同何望贤老师一样,他也不使用卡片,不看教案。但他是把所援引的内容一一写在黑板上。他的字,清丽俊秀,非常漂亮。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是看所引何文,而是在欣赏他的书法。何权衡老师课堂上总是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但他却时时习惯地瞥一眼讲桌上的卡片或教案,略显一些拘谨,令人感觉还有许多更为精辟的东西没有完全讲出来。后来,温绎之老师讲《张衡.》,说到张衡“博闻强记,娴于辞令”时,我便很快联想到这几位斋房里挑灯备课的老师。确实,不少同学也都把这几位老师当作了可以接近、值得效法的“师”与“范”了。每当我黄昏时分奔向七号楼,抑或深夜走出七号楼赶回宿舍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将眼光瞥向灯火闪烁的东斋房,心里便默默念道:我们尊崇的老师一定还在备着课,他们就像这不息的灯火,燃烧着自己,为我们的事业、人生引航。
这一组近代建筑,如今都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近百年来,她们身上的一砖一瓦都有着诉说不尽的故事,也给一届一届走出校门的学子带来永无穷尽的回忆。她们都是极富生命力的老人,辛勤地把河大精神深深种植在一届又一届学子们的心田。
大师级教授的风范
中文系教授中,李嘉言先生的名字是早被同学们熟知的。我们都知道他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副系主任。他兼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的编委,还领衔国家级项目《全唐诗》的编纂,当时,又要给我们讲授《楚辞》。工作、教学、科研三幅重担一肩挑,实在是辛苦。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李先生刚一走进教室,全班同学就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那段时间,李先生有些劳累,讲课都是坐在藤椅子上,偶尔站起来板书。他声音不大,但却能送到教室后排同学的耳朵里。有一天晚自习,是孙先方老师的辅导,李先生突然来了。他说他感到今天课堂上有个地方讲得不太透,可能会影响同学们的理解。说着,就讲了起来。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讲完了。他站起身,朝讲台下摆摆手,径自走了。就为了这十几分钟的补充,李先生摸着黑,从远在校外的家里巅巅地跑来。同学们感动得许久都没说出话。李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时,曾随著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研究国学。《楚辞》是他师从闻一多先生研究的长项。但他的《楚辞》教学从不以专家、权威自居。在串讲《楚辞》章句时,李先生总是先把其他学者的观点——相近的、相左的给大家一一介绍,然后讲自己的观点。比如讲《离骚》,他甚至还把同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的历史系教授孙作云先生的一些重要文章介绍给大家。但在课下,同学们议论时,还都是采用“李说”。
于安澜教授没给我们年级教过课,但是,他给我上课无数。一次,我在北土街的古董铺里买到一方有狮纽的寿山石印章,磨去原刻后,请于先生给我刻方姓名印。于先生看了石头,有些不高兴。他惋惜的说,石头一侧尚未磨去的边款上有“小松”二字,说明原刻为清代西泠八家中著名篆刻家黄易。“你好大胆子,黄易的印你都敢磨掉。可惜了!可惜了!”又说,你磨掉黄易的作品,让我刻。我哪能比上黄易啊!于先生告诫,再遇此事,要先看边款,了解刻家,再看印面,进行欣赏。无论谁刻的印,人家都付出了劳动,倾注了心血,不可随意磨去。后来,听两位篆刻家——王启贤师兄和王海师弟讲,于先生也都曾对他们进行过此类训教。那起因,想必就源于我的磨印。
我在开封地委工作时,有一次,被于先生唤去做陪客,接待参加书法大赛却名落孙山的雷云霆等三位书法家。固始的雷云霆先生写得一手小楷,新乡的一位先生写魏碑。看他们展示的作品,都足见深厚的功力,但不知何故落选。三个人都颇显沮丧。于先生说,他们(组委会)叫我写(书法作品),我就写了送去。后来啥结果,也不问。“我是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啊!”说完大笑,频频敬酒。于先生鼓励说,看了几位的作品,觉得很规整,底子扎实。于先生说,他曾建议,参加书法大赛的,无论所写何体,都应交一件楷书作品,以观其基础。他说,他对书法基础还欠工夫就急着进行行书、草书创作的做法很不赞同,但是据说这些人有的还居然得了奖,真叫人大惑不解。席间,于先生多次宽慰三位书法家:“做好自己的事儿,别太介意别人的评价。”
“做好自己的事,不介意他人的褒贬。”这是于先生多次给我讲的“哲学”。他一生就奉行这种“哲学”。于先生一生没有在书画组织里担任什么要职,也不计较给他评几级教授,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认认真真地做他的学问,写他的小篆,刻他喜欢的印章。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写的《汉魏六朝韵谱》,由国学大师钱玄同、刘盼遂为之作序,王力撰文写书评,称之为填补学术空白 之作,至今仍被学术界认为是鲜有超越的扛鼎著述。先生的《画论丛刊》(白石老人署签、郑午昌先生作序,黄宾虹先生写书评)、《画史丛书》、《画品丛书》在全球影响更大,被研究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艺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论史者列为必读书,还甚至被研究西方文论史的学者如伍蠡甫先生等,选为重要参阅书。于先生的主要著作还有《古书文字易解》、《诗学辑要》、《书学名著选》、《书法源流表》等。这些书著,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大同时期教授中,写出那么多而厚重,那么大的影响而难以企及的著作者,唯于先生。我时常想,倘若有十位于先生,北大中文系就会被超越;有五十位于先生,河南大学的排名一定会越过北京大学而跃入世界名校之列。
但是,长久以来,于先生一直是三级教授。对此,我很为不平。我同时为之不平的,还有任访秋、王梦隐教授。那时候可能是“政治”包袱太沉重的缘故,任先生总是微驼着背,戴着一幅深度近视镜给我们上课。他曾给别的年级讲古代文学史,给我们则是讲篇子——古代文学作品选,也给我们讲专题《龚定庵文学略论》。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老是让任先生“打杂”,而不是提供条件,让他去做他的近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但是,无论什么课,任先生都是认认真真地备课,仔仔细细地讲授,勤勤恳恳地在三尺讲台上耕耘着,固守着“倾其所知,以飨学子”的心态。
入校时,王梦隐先生还是学校图书馆的副馆长。馆长张邃青教授会议、公务、杂务事情太多,图书馆工作就由王先生主持。后来才知道,我那时受益最多的最佳去处学生参考室(我们惯称阅览室)、文科阅览室(又称文科分馆,在十号楼。十号楼二楼大厅还设文科报刊阅览室),都是王先生建议设置的。王先生讲课是有板有眼,慢慢道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听他讲《某公三哭》。那是著名书法家、诗人、宗教界名人赵朴初先生“反帝反修”的新作,近似小令散曲的形式。王先生慢慢地念着,有些像吟诵。同学们很感新鲜,真希望王先生能放开喉咙,纵情吟唱一番。王先生也很投入,讲到激动处,他用左手摘掉眼镜,三个指头撮着镜架、镜框结合部,随着慢慢的吟诵,慢慢地画着圈儿;头,也微微的摇着,摇着····但后来却让他到艺术系讲语文课去了。艺术系的语文课,其实比高中的课深不了多少,讲是好讲,要命的是批改作文,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多的作文本,真不知王先生熬了多少个夜啊!这种课,其实是普通讲师就可以胜任的。但对着美术专业、音乐专业的学生,王先生依旧是认认真真地备课,慢慢的给他们讲解着。又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听说又让王先生去对口县,给那里进修的教师讲课去了。评定正高级职称时,评审组抱怨王先生的著作不够丰富。所以,正教授的帽子就长久的在他头上悬着。而王先生,依然是在给他指定的临时岗位上,认认真真地备课,慢慢的讲着····
还有一位没给我们上过课,甚至已经从学校教师花名册中清除的教授,原名叫李象贤,那时叫李白风,又自称李逢。他那时在学校西边的土地庙街(“文革”时改称铁塔二街)住,负责扫附近街道的“马路”,接受街道上革命老太太和红色退休工人们的监督、改造。正像他的一方自用印的印文所说,他本是“三十年代新诗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成为与他的文友叶圣陶、茅盾、郭沫若、柳亚子、臧克家、施蛰存、端木蕻良等齐名的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某大学选编出版的“五四”以来新诗选一书中,李先生入选诗作的数量在郭沫若之上。他还是书法家、篆刻家。他的金文体、楷体书法和篆刻,绝对是国家一流水平。郭沫若、柳亚子、臧克家对他的书法篆刻都有极高的评价。但在我们上大学之前,他早已经被划为“右派”,潦倒得“十年不制衣”(李先生自用印)了。他没有被难以抗争的逆境压垮。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他一边读书学习,一边督促下班回来、同样是疲惫不堪的儿子,完成当天的学习计划。他还要为前来求印、索字、学字的朋友们刻着、写着、辅导着。即便如此,他还是开出单子,让在河大工作的小友佟培基到河大图书馆替他借书。他每天都在艰难地挤时间写作,最终完成了《东夷杂考》、《古铜韵语》的著述。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刘朱樱老师唤我去整理《李白风印谱》,准备出版。看到李先生在逆境中刻制的那么多篆刻作品,我的灵魂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这些教授,辛苦一生,勤勉一生,为我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是我们尊崇的文化艺术大师和教育大师。他们修身、治学、授业的点点滴滴,都展示出大师的高尚风范,体现出可供我们效法、继承的煌煌灿灿的河大精神。
党务工作者的本色
退休前,我再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后来,以党务工作者的身份在高校退休。在岗位上时,我常常忆起母校的韩倩之书记、赵文山副书记等党务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并且时时效法。
至今,我对“文革”时所有派别强加给韩书记、赵书记的污言秽语持不屑的态度。我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记得,那是1965年的春季,我在韩倩之书记带队的“四清”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时,突然得了急性喉炎,高烧不退,汤水不进。韩书记很着急,紧急联系中牟县“四清”总团要车。不巧的是,仅有的一部汽车在外出差。韩书记立即派他的高个子勤务员张有发背着我,去十余里以外的火车站,送我上车,回学校治病。到开封车站一下火车,我看到赵书记和校医院的大夫、护士在站台上接我。当时,我不能说话,却激动得大哭起来。赵书记安慰我说,韩书记给他打了电话,要他带着医生、护士火速赶到车站来接我。先安排在学校医院治疗,如果不行,就转市医院。在学校医院打上针,很快就退烧了。护士取笑我:“大男人,在火车站当着那么多人哭,还哭那么痛!”我说,我的母亲刚刚去世,还不到半年····一天后,学校党委办公室一位老师来病房看我,询问病情。他说,韩书记打来电话,问你的治疗情况,让你安心治病,不要急着回去。
“四清”结束,我们年级又接着进行军事训练。那时,我已经病愈半年,身体恢复得很不错了。一天,学校领导慰问参训官兵和学生。赵书记和学校武装部的张鋆部长走到我面前,仔细查问身体和训练情况。赵书记说,不怕吃苦,这很好。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实在坚持不住,就对我说。你身体素质不太好,别硬撑。他对围上来的同学说,你们也一样啊!
那时候,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每个年级都选配了辅导员。刚入校的时候,辅导员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在熄灯铃响之后,将滞留在教室、阅览室及路灯下读书的学生劝回宿舍休息。因为当时口粮供应不足,学生身体素质普遍偏低,学校要求学生停止激烈的运动,注意劳逸结合,保证休养生息。我就曾数次在不同地方被劝回过。
我们年级派来的辅导员是邹同庆老师和上届留校的李善修老师。邹老师原来在《全唐诗》项目组,从那里抽调出来,足见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两位辅导员一到职,就搬来我们的乙排房宿舍。这便于他们随时发现情况,解决问题。他们不搞说教那一套,也没有以上对下的那种凌人盛气。他们对同学和气、亲切,关怀备至。同学们谁也没把他们“外气”,对他们如兄长一般,无话不谈。学生们的家庭困难、思想压力、入党要求、恋爱风波、学习困难,都在他们平时的宿舍聊天中,了解得一清二楚。后来,“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文革”将近,“山雨欲来风满楼”,同学们的心情紧张起来,但这也没影响与辅导员之间的互信关系。大家对两位辅导员依然是没有猜忌与戒备,辅导员仍亲切地和大家一起谈学“毛著”心得,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谈一位留苏学生痛批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即便是“文革”中彼此观点、派别不同,双方也没出现横眉怒目、拳拳相向的局面,也仅止于直接对话、交换意见而已。
长期以来,不少人一直认为,高等院校从党委书记到辅导员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说执行了极“左”路线,整了不少人,迫害了不少的有才能的教师。我不全苟同。路线是上边根据彼时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而制定的,是与非、功与过的评价一直在进行着。学校的党务工作者工作做得如何,看看毕业的学生也就知道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包括高等教育时期,也包括高等教育前时期;既包括高校内的若干系统,也包括高校外的许多系统。在高校内部,教授们是尽可能多的让学生掌握知识,获得技能;党务工作者则除了保障教学,重要的是要以高尚的精神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光辉的榜样影响人,还要防微杜渐,尽可能防止青年学生在思想上、行为上初露的不良根芽。他们异曲同工,都是呕心沥血地教给学子做人、做事、做事业的准则与方法,传授继承、弘扬河大精神,为国效力的本领。
······
写到这里,母校的人,母校的物,母校的事,一个个、一件件、一幕幕涌向心间,令人不禁心潮澎湃、热泪滚涌:母校啊,我这一生,最为骄傲、最感荣幸的,就是您用百折不挠、拼搏向上的河大精神铸造了我的灵魂!值此母校百年华诞之际,我要打心底高喊一声:
感谢你,我亲爱的母校!我亲爱的河南大学1
2012年5月6日――6月10日于郑州大学汉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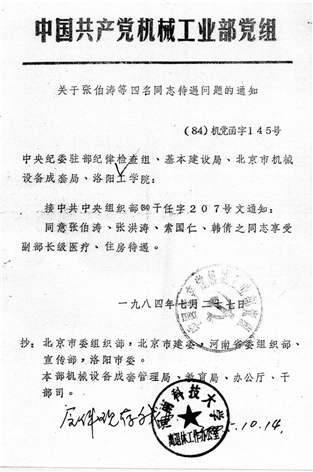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