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京平博士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关于这个案子,我想说几点笼统的意见。
一、不同的经济案件或者经济犯罪案件,应该有不同的司法处理模式。涉及到集资类的案件,通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集资类的案件或者融资类的案件可能涉及到刑事追究的时候,或者不涉及到刑事追究的时候,我个人总是感觉到有时候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力量,或者司法机关起诉刑事追诉的时间不太恰当。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因为通过了解了一些这样的案件之后,我们发现其实这样的案件如果按照经济规律,如果按照其他的部门法去协调、调整,按照其他的法律处理,恐怕不至于出现事后的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现象。
所谓不想看到的现象,比如说融资的老百姓资金原来可能是有一定保障的,结果因为行政力量的介入,或者因为司法力量介入时机的不恰当,导致了这些资本安全反而受到了影响。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你的本意或者动机,我们假定是善良的,是希望保护融资群众,参与融资、集资的老百姓的财产安全的,但是可能最终的处理结果反而不好。这种不好不仅涉及到参与集资老百姓的财产安全,恐怕与政府有关,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错安在政府身上的手,本来就是错安的,结果伸的又特别长,管得又特别多,当然也包括司法。
这是我的第一层意思,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在刑法上通常特别强调刑法的迁移性,我们更多的强调是利益,但是在司法领域也得强调刑法的迁移性(音),当一个案件发生以后,既可以按照经济规律和其他部门法处理,某种意义上你也不能说没有启动刑事追诉的任何事由,或者程序性的事由,他都有。但是要甄别,要从中间作出一个恰当的、科学的选择,哪一种处理方式先行,既保证了老百姓财产的安全,又保证了工程能够按照原来的设想,或者大致的发展方向安全的发展下去,各方的利益都能够达到最大化,这是我要说的一点。
二,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讨论罪非罪的问题,因为毕竟不了解本案基本的事实。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严格依照司法解释办案,或者说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细化法律规定的司法解释办案,这是我们各级刑事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则。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基本规则呢?因为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反复强调,通过一个文件强调,任何刑事裁判应该将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作为裁判引用的依据。除了法律、法律解释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以外,还要注意其他的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性说理依据。为什么说这样的问题呢?裁判的引用依据毫无疑问与2011年1月4号开始实行的这个司法解释有关系,关于适用192条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写的非常清楚。一共列举了8项具体的行为方式,或者应该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还有一个兜底性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办理这样的案件,或者认定他为集资诈骗,认定为集资诈骗犯罪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就得围绕着这样已经确定的细化规则进行刑事证明,这个刑事证明的过程必须围绕着这个。
本案是否严格依照这样的规则去进行刑事证明,最后拿出来判决的结论?因为我没有看到判决我不敢说,但是我下面想强调这么一种情况,我们的司法规则特别是刑法规则,实际上是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态度在不断丰富,所谓不断的丰富就是说刑法规则里头除了我们常见的刚才反复强调的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还有普适性的规范文件,之后还有局域性的规范文件。现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态度,就是要强调案例的指导作用。那么我所要说的是什么呢?指导案例制度下并不是只按指导案例,因为在指导案例出台之后,或者出台之前,我们还有大量的其他参考案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厅颁布的案例,或者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有了一定态度的案例。
7月4号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通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专门网站,这个网站会不断的公布一些新的案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毕竟湖南某种意义上相对于比如浙江,某些沿海地区,经济特别活跃,民间融资活动特别活跃,特别普遍的地区,他属于欠发达地区。那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经济活跃地区产生的一些案例,或者案例里头的裁判说理部分,应当作为其他地方裁判的时候参考的重要规则。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浙江围绕着某些典型的案件,司法机关裁判里头所表达出来的那些意思,也就是说甄别哪些属于诈骗哪些不属于诈骗,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案例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里已经确立的规则再进一步细化。那么再进一步细化后的规则,因为案例的参照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自发秩序,不是说案例里头有一个非法集资的案例我们就参照它,他只要说理依据非常充分,而且他的说理是与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或者普适性的规范文件都是吻合的,他就有参照的生命力,也就应当参照。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看现在发生在湖南的这个案件,那毫无疑问恐怕在裁判说理依据方面,在裁判说理的程度方面恐怕都是非常欠缺的,也就是说你说理不透彻、不充分,某种意义上反推回来,可能是法律适用本身有的问题。或者法律适用不足以让我们相信你的法律适用是符合最基本的法律规范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三,关于死刑,在死刑的问题上,特别是在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上,再具体到192条适用死刑的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包括去年很多典型案例出现的时候,一些内部研讨的场合我就说过类似的话,在死刑的问题上,死刑的政策应该服从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是国家最基本的刑事政策。而死刑政策是宽严刑事政策里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关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早在最高法院很多年前已经确立的《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文件》里,对死刑的适用,在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又有了严格的限制。说的严格一点,死刑按照宽严相济刑事的案件,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公司。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包括国家保留死刑、限制死刑、减少死刑的适用这些具体的描述,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应该在类似的案件里头,要遵从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宽严相济和死刑政策里,来决定一个案件的刑罚处理。或者换句话说,我个人向来主张在死刑领域,法律的适用应该服从于大的政策,不像其通常的、一般的、普通刑事犯罪的查处,在贯彻政策的中间必须以法律适用为基础。尽管本案已然如此,但是我们要总结经验,以后再碰到这样的案件怎么办?再一个就是规则,说白了现在如果要想让这个案件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更好的其他的双方都可接受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我们能不能从规则丰富的角度再拓宽一下视野,其实办案的律师或多或少也有这层意思。有时候我们寻找规则,找着规则告诉他这个规则是可以用的,或者某一个典型案例,最高法院已经有明确态度了,里头判案的规则,说理的规则可以拿到这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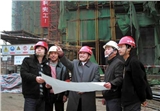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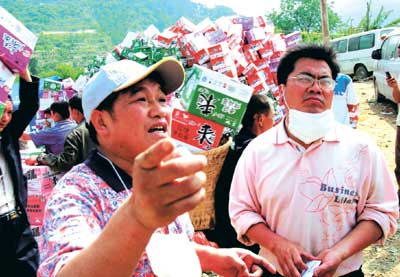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