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民主的基石 (四)
四、民主的基础应该是依法治官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一方面吸取国民党的教训,一方面总结自身积累的政治经验,建立了以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制度。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1953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普选,人民自下而上地逐级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经间接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民为主的国家。《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人也都熟悉这样的说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换言之,民为官主。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而且地区性差异较大的国家,不适宜采取直接民主的模式。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属于间接民主的范畴,因此,实现民主的要点和难点也是“代表性”问题,即如何保证执掌国家权力的人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共同信仰的政党。共产主义理想是要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道德的整体高尚,从而达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毫无疑问,这个理想是美好的,这个信仰是崇高的,而美好的理想和崇高的信仰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应该是重义轻利和克己奉公的道德楷模。在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许多共产党员就是在这一理想和信仰的引领和激励下,抛弃私利投身革命,甚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秉承这一理想和信仰,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党员干部,提出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倡导“大公无私”的行为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以理想和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规范确实很有成效地约束了政府官员的行为,也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一般来说,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人都是比较高尚的人,而担任了领导干部的人也都会用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社会精英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老百姓也体验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德为本”的民主。 然而,权力具有极大的腐蚀性,依附于权力的物质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它们可以弱化人的理想信仰,也可以松懈人的道德约束。毋庸讳言,随着共和国的年龄增长,特别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荡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之后,共产主义的信仰在有些人中间逐渐弱化,一些人入党的目的不再是“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是要获得更好的个人前程。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也促进了人们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道德对官员的约束力不断减弱,“民为官主”有时就变得徒有虚名,一些“人民的勤务员”也就忘记了人民。 如前所述,民主不能仅以道德为基础,必须建立法律制度。诚然,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也着手修建法律制度,但相对来说,法制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道路是曲折的,期间还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大民主”,因为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实现其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然而,这种在“无法无天”的形下推演的“大民主”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也是巨大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会议公报,这次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会议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中国重新踏上了现代化发展之路。1980年3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加强了党内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中国人深切地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发展民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民主发展的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民主政治建设既不能滞后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此,发展中国的民主,既要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也要考虑中国的社会现状。这应该是一个渐进增加的过程。中国不能搞“休克式”民主改革,而应在现有民主“存量”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突破性改良,不断扩大民主的“增量”。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邓小平强调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人民民主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保障和实现,这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遗产之一,也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路线。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一举通过了七部法律,拉开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序幕。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一次明确用“法治”代替“法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述重大事件记述了中国法治进步的轨迹,也反映了中国人法治理念的提升。 推行法治有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是立法,其二是施法。虽然有法律未必有法治,但是无法律肯定无法治,因此,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其实,立法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工作,特别是当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的时候,其他国家的立法工作就可以借鉴或移植,甚至在某些领域内可简化为法典的翻译。然而,法律实施是比法律制定更为困难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有着长久而且深厚的“人治”文化传统,那么要想把写在纸上的法律转化成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要想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养成按规则做事的法治行为习惯,那绝非一蹴而就之事、一朝一夕之功。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标准不是立法,不是法律的健全程度,而是施法,是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情况。无法律当然无法治,但是有法律也未必有法治。中国法治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法律够不够用,而是法律管不管用。面对这种状况,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表明,中国法治发展的重心从法律制定转向法律实施。 现代法治的精神在于治理那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或者说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官员。当然,老百姓也要守法,但是对于法治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官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手中掌握的权力。香港大学陈弘毅教授在谈论立宪民主制度的时候说道:“第一是法治的概念,这主要是指统治者的权力受宪法和法律所限制;政府的权力是宪法和法律所赋予政府的,政府行使权力时,受宪法和法律约束;政府的运作,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由此可见,法治的主要功能就是治官限权。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大会”上讲道:“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人类群体性生活的产物。在群体生活中,共同利益需要一些人行使指挥权或决策权,其他人则要服从。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人际关系就是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侵蚀性,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必须加以限制和约束。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休止。……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表现之一就是贪污腐败,而预防腐败也是民主制度的一项基本功能。俞可平教授也指出:“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和专权。这是政治学的一条公理,也是民主治理的一个基本要素。”治官限权体现了民主功能与法治功能的契合,而防治腐败则是二者的共同目标之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转型,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并有一定程度的蔓延之势,国人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也不断加强,反腐败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2012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01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向媒体表示,反腐败方面的立法已在进行调研。同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做工作报告时又提出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国家监察法》。这是我国反腐败立法的重大进步。但是,《国家监察法》只是反腐败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反腐败立法还存在较多缺欠,我们不能企望一部《国家监察法》就解决反腐败的所有问题。我们还应该继续修改或制定其他的相关法律,形成一个完整且能有效运行的反腐败法律体系,而且要在人民关心的问题上有所突破,例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问题、国家资产与公务经费的公开与监管问题、行政决策的信息公开与民众监督问题、领导干部选任的信息公开与民众监督问题等。总之,反腐败立法的完善既是推行法治的需要,也是实现民主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才逐渐成长壮大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的,因此,不忘“初心”,就是要不忘人民,就是要牢记“民为官主”的道理,就是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中国的民主发展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而且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没有法治的基石,民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孔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笔者斗胆套摹:民主者,国家之大本也;法治者,国家之达道也。致民主法治,官民位焉,世人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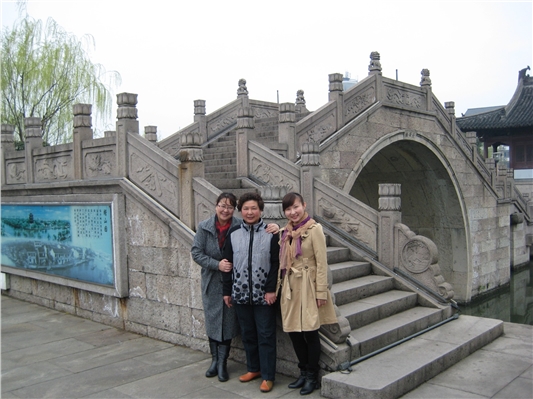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