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回家
一九五四年,朝鲜停战,安东防空司令部随即撤销,上级又调我到沈阳防空司令部工作。
这一年,中央下达了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的精神。为了保证义务兵役制的贯彻落实,领导又安排我带队到辽宁省北镇县训练兵役干部。这期间,我一直是副营级待遇。
我和爱人结婚时,领导是一再征询我们的意见,说家属可以当兵,也可以随军。那时候要是能想的远一点,家属也就当兵了。使她这个一九四六年就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工作过的老兵重新回到部队,到晚年也就可以享受到离休待遇了。很可惜,人的一生有多少次这样好的机遇,你如果把握不住,就这一念之差,机会就从你身边擦肩而过了。
供给制时期,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一直处于优越的位置。即使后来实行了薪金制,我的工资是职务加军龄,也算比较高的。到北镇县训练兵役干部时,我的官也就算大了。上小灶吃饭,有勤务员照护,家里顾有媬姆,买点东西有人帮忙,就连孩子们上学也有战士们帮助接送。白面、大米、鸡、鱼、肉、蛋常有,这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女儿宁宁,一种满足的感觉油然而生。应该说在北镇县那个阶段的生活是非常优越的,也是我以后经常留恋、难以忘却的。
北镇县武装部部长是一个在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老家伙,比我参加革命还早半年多一点,算是红军时期的个老同志。心高意大,蛮横的无理来三分。满北镇县似乎没有一个他能看上眼的,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办公桌子上放着酒瓶子。有事无事地灌上几口。哪儿通知开会他也不去。不高兴时就扯开嗓子在院里叫唤上几声,算是他开会安排工作了。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对我却是特别的关爱,我一去北镇县武装部,他就知道我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他还给人介绍我是真刀真枪地和日本人干过的。这些情况我估计是辽宁省军区事先与他打照呼的。他不谈工作,先说喝酒,很是隆重地招待了我一番。
他对我说:“来了啊!来了就住下,想吃咱这儿有有名的“沟帮子烧鸡”,那可不。想喝么?这“辽河大曲”就不错。兵役干部么?让他们训练去,你、我咱们哥俩都甭管。哼!咱们他妈的打日本人那会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咱们是什么人?咱们是功臣!知道吧,功臣就是有功之臣,有功之臣就要享受。那可不,在北镇县这地方,我是老大,你就是老二,别看他们给逑了咱兄弟不大的个官,哼!他们都得听咱的,那可不。“山西王”。知道吧?
他是黑龙江人,别看外表豪放粗犷,嘴皮子却挺巧,说话一套一套的。有个得意的口头语:“那可不”。我奉称他为“黑老大”,他管我叫“山西王”。我含含糊糊地应酬着,他爱说什么就说去,管那些干吗?鬼才研究他说的那些歪理对与不对呢?
“黑老大”工作自有一套,无论大事小事,不和他的那几个副手商量,而是和我说。我猜想这其中原因一:我是辽宁省军区派来的,可能上面对他有交代。原因二:整个武装部就数他和我资格老。
一九五四年十月,上级让北镇县武装部派一名部级干部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设在汉口的一座步兵学校学习,他对我说:“山西王,你去。你有文化,又年轻。出去学两年,回来在咱这儿干,不比你回省军区差,做副部长比他们强,那可不,他们不行”。
天啊!平生第一次听到有人夸我有文化,我有什么文化?也就是五零年在部队速成识字时认了几个字,或许在他眼里我确实是有两下子?
地方武装部是军人,可他和野战部队不一样。在野战部队时,上下班碰到个领导,敬个礼,说句首长好就走了。碰到下级时,对方也是如此,彼此之间谁也不在意。可一个县里的武装部,每天的工作是尽和群众打交道,讲究的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熟悉,人与人的交际,就连每天出入上下班的感受都不一样,碰到熟人你必须是站住有话无话地啦上几句,那样才能说明互相厚道,有深交。我,我没有这个本事。
县城很小,每天能看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乡间老农。每当看到他们,我就联想起了家乡的父亲和三叔,他们弓着腰弯着背,扛着锹、镢、锄、耙的身影不断地在我眼前恍惚。北镇县的乡土气息,勾起了我一次次地对家乡的怀念。
“黑老大”没有瞎说,他确实有这个本事把我送到军校学习,锦州军分区同意了他的意见。我,却谢绝了。
到一九五五年二月,锦州军分区领导找我谈话:“中央决定,全国的县武装部即将改编为兵役局,归地方管理。和平时期,军队要缩编。你的工作一是就留在北镇县兵役局当个副局长。二是转业到东北地方工作。老同志了,任你选择”。我,又一次谢绝了。
机遇,很好的机遇,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在我身边溜走了。人都说:成功=天赋+勤奋+机遇,可我却是机遇来了又都让它走了。
“安排你上学你不去,留你在我这儿工作你不干,转业地方吧,你也不走,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山西王,你给我说”。直火得“黑老大”一个劲地在叫唤,说话的语气咄咄逼人。
为什么?为什么?
我想干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家,我想回家!
我从一九三八年的四月离家,至今已经整整十八年了。
一个回家的念头萌发了,而且是十分强烈的。我恨不得一步就回到自己的家门,抱住我的父亲、我的三叔对天长喊一声:“爸爸、三叔啊!我回来了!”
这么多年了,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呢?前几年在西安时曾给他们邮过点东西去过一封信,说祖国解放了,我这就回去看你们,侍候你们,哪儿也不走了。可谁知朝鲜战争又开了,没有回成。现在朝鲜也停战了,我还犹豫什么?还在等什么呢?
家里的两个孤寡老人想来也快八十岁了,仅有我这唯一的亲人却不用说依靠沾光,十八年是连一面也见不上。他们恐怕早就是以日度年、翘首以待焦急地等盼上我了。我是该回去尽点孝了。
为人之道,为国尽忠、为父母亲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为了祖国解放,我从南向北,从北向西,从西向东,当了十八年兵,打了十八年仗。现在解放了,回家尽点孝,这难道还有什么非议吗?要议你就议去吧,反正我是非回家不可了。
于是,我就打报告,找领导要求批准我退伍回老家。许多领导和老同志都希望我留在东北,我却一一谢绝了。
行,既然你老王坚持要回家,成全你,就让你回家。反正这地球离了谁也要转动,咱这里少了谁也照样要发展。
在锦州附近的高桥镇办了复原退伍手续,领了三千六百块的人民币,就结束了我的全部军旅生活。
看看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步,“黑老大”自知无力挽回,急急忙忙地从北镇县赶到高桥镇,给我买了一只手提皮箱,高桥镇这个地方可能离海不远,水产品不少,又买了些水产品,扬扬手,算是敬了最后一个军礼,送我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十八年!十八年的军旅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按照当时的政策,像我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留在山西省城太原或平遥县城工作的。一路上,老婆叨叨絮絮地说个不停,希望能留在城市好安排个工作,可是我回家的念头发了疯,一点也听不进去。
美不美,是家乡水。亲不亲,是古乡人。一路走,一路吵。就这样吵着、闹着,回到我告别了十八年的家乡——山西平遥南政村。
关于家乡名字的来历,翻阅过许多资料,无考待查。小时候,在学堂曾听一位教书的老先生说过这样一段故事:
当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时途经平遥,先在城东二十里安营下寨,而后驾道游驾,平遥地方县官为讨好慈禧,令前方沿村清水洒街,黄土垫道,备好道路迎接。
在慈禧当时计划要路过的一个村庄,聚集着许多闹事的平民百姓,地方为怕引起麻烦,只好放弃原来准备好的道路,改道绕行进城。
慈禧不高兴地责问县令,为什么备好的道路不走?改道绕行呢?县令那里敢隐瞒真情,连忙跪下具实奏道:“禀告老佛爷,原来准备路过的一个村庄,小人没有治理好,有一伙刁民要拦驾寻事,所以只好改道”。
慈禧见县官所奏尚属老实,逐信口说出:“如此说来,这个村庄实属难治,不怪你,起来吧”。
这位老先生讲的这一段故事是否可信?我不能断定。但平遥境内确实有南营、北营、新营、游驾、道备、难治村这些村名。
我的家乡南政村,地方语中就叫难治村。顾名思义,就是很难治理好的一个村子。解放六年多了,家乡还是那模样,比我记忆中的南政强不了许多。
魁星楼早拆的不见了,庙宇里奉供的神像破烂的有鼻子没眼、缺胳膊少腿,村东、村西的门楼也快要塌了,街道上橛子车轱轳碾压出的两股车辙坑坑凹凹地,有一团没一团地涌济着污水,发出了一阵阵呛人的臭味。
父亲、三叔的身体还算可以,只是更老了许多。院子里的三间旧房已经彻底倒塌了,而且为了生计,父亲已经将其中的一半卖掉。在南面有用泥砸半块砖盖了一间小房,那是我走以后三叔居住的地方。
只有院里那棵槐树它长高了,枝叶也很茂盛。人们不是都说大树下面好乘凉么?那,我就是大树,父亲、三叔你们就享受吧!
童年时代的朋友木头塞塞、雀[QIAO]日、石塌天也过来看我,他们没有多大变化。只有神拍六日,因为在日伪统治时期帮人家做过一些事情,而今落得下落不明了。
历史啊!就是这样,有时它能使一个坏人变好。有时它也能使一个好人变坏。我们一块欢聚,一块畅饮。今天走东家、明天去西家,着着是美美地高兴了它几天。
而几天过后,温度降了下来。算了算,我那三千六百块人民币已经留下不到三千块了。我才三十八岁呀!总不能就这样呆下去吧?还是面对现实吧。
我有一个堂弟叫王忠,在村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副社长,人很精明,他见我出去当兵这么多年,做事还是那么没谱,就劝我少和那些旧时的朋友每天大吃二喝,赶快找个工作吧。
我这才想起从部队回来时部队给山西省民政厅开的介绍信,我们哥俩先去了县里的民政科,民政科长说这个介绍信交给他就行了,不需要去太原。反正平遥也缺干部,你先考虑一下干什么合适吧,过几天再来,咱们研究安排你。
要我考虑干什么?这不是废话么,我能考虑了吗?我知道你们地方上哪里缺干部呢?
我也不是就没有考虑,我是在考虑我能干了什么?我以前杀过猪、赶过马车、杂货店当过小跑、织布厂织过几天土布、再就是当兵打仗、打仗拼命,所有这些行道,地方上哪儿能行呢?
隔了几天,我和堂弟又去了县里民政科。那科长很热情地问我考虑的怎么样?我说我服从组织分配吧,去哪儿都行。
民政科长说那好,他们已经商量过了,县里人民医院缺个支部书记,你就去那里当个支部书记吧。职务么是安排的低了一些,不过医院很快就要发展,你先干着,你的职务还可以进一步变化。
医院?医院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可并不陌生,部队就有。那里尽是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清高人物。我不愿意搭理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和这种人接触,再说,我这两下子能领导了他们么?
我一听就不假思索地对那位民政科长说:“不行,不行,医院我可不去啊!你不用给我考虑职务,还是在农村给我考虑个工作吧,我农村出身,文化水平低,当什么支部书记呢?干个其它的吧”。
又过了一个多月,民政科长托人捎话让我再去一趟县里。他对我说:“原寺供销社缺个主任,你看去那里行不行?”他怕我嫌弃,还加了几句鼓励的话:“老王,知道吧?平遥四百零八村,原寺,岳壁、难治村。原寺可是平遥的第一大村啊!”
我想也不好再麻烦领导了,说:“那就去原寺吧。主任不主任不要紧,有个工作做就行了”。
就这样,我当起了一个总共只有三五个人的农村供销社主任。
我原来在部队时每月工资是一百三十多元,而一个基层供销社是低的再不能低了的企业单位。我当个主任才是行政二十四级,每月只领四十块,其它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四十块!就是这个四十块!我这个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一直干到我一九六六年退休为止,再没长过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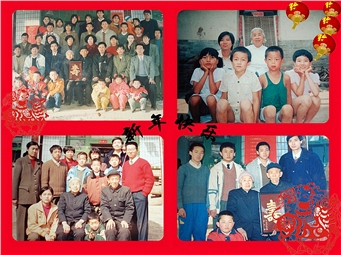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